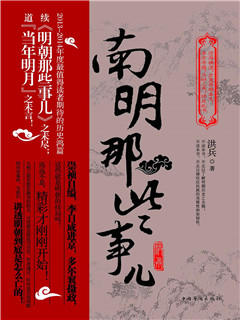- [ 免費 ] 第壹章 詭異
- [ 免費 ] 第二章 抉擇
- [ 免費 ] 第三章 國策
- [ 免費 ] 第四章 疑案
- [ 免費 ] 第五章 湮滅
- [ 免費 ] 第六章 抗爭
- [ 免費 ] 第七章 雄起
- [ 免費 ] 第八章 困境
- [ 免費 ] 第九章 殘夢
- [ 免費 ] 第十章 內訌
- [ 免費 ] 第十壹章 驚變
- [ 免費 ] 第十二章 敵後
- [ 免費 ] 第十三章 中興
- [ 免費 ] 第十四章 危局
- [ 免費 ] 第十五章 南下
- [ 免費 ] 第十六章 後方
- [ 免費 ] 第十七章 整頓
- [ 免費 ] 第十八章 反攻
- [ 免費 ] 第十九章 合流
- [ 免費 ] 第二十章 密謀
- [ 免費 ] 第二十壹章 敗局
- [ 免費 ] 第二十二章 滄海
- [ 免費 ] 第二十三章 殉難
杏書首頁 我的書架 A-AA+ 去發書評 收藏 書簽 手機
简
第十七章 整頓
2018-9-27 20:44
四川亂局
孫可望決定不鳥朱由榔,自封為“國主”甩開膀子單幹。在白文選、王尚禮、王自奇等親信的支持下,孫可望以微弱的優勢暫時摁下了李定國、劉文秀,漸成“壹家獨大”之勢。
不過,出滇抗清不是壹件容易的事情,孫可望的實力是有的,但面臨壹個很現實的問題:怎麽去?
廢話!那時候又沒有飛機,當然得走過去。——既然不能飛過去,麻煩就大了!
雲南地處西南壹隅,從這裏出兵抗清有兩條路:壹是東出貴州,進入湖南;二是北抵金沙江,順流穿過四川,進入湖北。但是,貴州、四川名義上服從永歷政權的領導,並不是孫可望的地盤。
——他們會給孫可望讓道嗎?
——即便同意借道,他們是否會趁虛而入,搗掉孫可望在雲南的老巢?
對於決心出兵抗清的孫可望而言,“攘外必先安內”既非托辭,也不是空話。盤踞在四川、貴州的這群鳥人,自己不抗清,還擋著別人抗清的路。不解決掉貴州、四川的問題,這仗根本沒法打!
貴州地域狹小,軍閥勢力也比較單壹。偏橋(今貴州施秉)總兵皮熊趁著孫可望率軍入滇,帶著壹群烏合之眾賴在貴陽做“土霸王”,僅此而已。就他那副“熊樣”,孫可望擡起壹腳就能踹死三回,不足為慮。
真正的麻煩在四川,這裏不僅地域廣闊,而且各種勢力犬牙交錯,比“浙系”、“閩系”、“地方系”攪和下的福建還要混亂好幾倍!
前面說過,豪格、吳三桂大軍壹路追擊孫可望,追到遵義府就追不下去了。由於肚子餓,決定班師回朝,只留下王遵坦、李國英鎮守四川,這是永歷元年(1647年)的事情。
清軍留守部隊兵力單薄,王遵坦、李國英當然不能遍地“撒豆子”,那樣只會被南明、大西以及當地的殘余勢力各個擊破。因此,清軍名義上駐守四川,實際上絕大部分軍隊都龜縮在川北的保寧府(今四川閬中)附近。這年十壹月,被委任為四川巡撫的王遵坦病死,由李國英繼任,依然將主力駐守在保寧,並不敢輕舉妄動。
除了保寧府屬於清軍控制以外,四川各地就比較熱鬧了,光是數得上號的就有七股軍閥勢力。
——川西有壹股,也是實力最強的,即盤踞嘉定(今四川樂山)、峨眉壹帶的楊展部。
楊展,四川嘉定人,崇禎十二年武進士,曾任明軍參將,大西軍入川後被俘。僥幸逃脫後,楊展在敘州(今四川宜賓)壹帶組織軍隊抵抗。隆武二年(1646)進抵嘉定、峨眉壹帶建立根據地,致力於恢復生產、發展經濟,成為當時四川全境唯壹自給有余的地區。
——川南有三股,分別是王祥、侯永錫和馬應試。
王祥,前明參將,後任遵義總兵。永歷元年(1647年)六月,王祥曾率軍進抵順慶府(今四川南充),命部將王命臣駐守,大肆盤剝百姓。次年,清夔州鎮總兵盧光祖、敘南鎮總兵馬化豹、永寧鎮總兵柏永馥率兵合擊順慶,王命臣潰敗南逃。此後,王祥便盤踞於遵義、江津、合州(今重慶合川)、彭水、黔江壹帶,與貴陽的皮熊遙相呼應。
前明永寧總兵侯永錫的兵力不多,主要在永寧(今四川敘永)壹帶活動。
馬應試原任瀘州衛指揮僉事,此時也拼湊出壹支武裝,盤踞在瀘州、富順壹帶。
——川東南有壹股,即於大海、李占春部。
於大海、李占春是南明重慶守將曾英的義子,曾英被孫可望的大西軍殘部殺死後,於大海、李占春便統率舊部撤離重慶,在涪州(今重慶涪陵)、長壽、墊江壹帶活動。
——川東北有兩股,分別是“三譚”和“搖黃十三家”。
“三譚”是指前明忠州衛(今重慶忠縣)世襲衛官譚文、譚詣、譚弘三兄弟,主要活動在忠州、萬縣(今重慶萬州)、夔州(今重慶奉節)地區。
“搖黃十三家”確切地說不算壹股,而是壹個派系眾多、組織松散的“聯盟”。“搖黃十三家”的前身,是打著“搖黃軍”的旗號,活動在川北地區的農民起義軍。遭到官軍鎮壓後,這些起義軍的殘部紛紛聚攏在川東北的三峽地區。雖然統稱“十三家”,實際上數量遠遠不止十三支。這些勢力類似於占山為王的“山匪”,互不買賬,各自為政,主要首領有袁韜、劉惟明、白蛟龍、呼九思、楊秉胤、景可勤、張顯等人。
四川內戰
四川的局面壹片混亂,既歸因於張獻忠垮臺之後的“半真空狀態”,也跟永歷政權委任四川官員的雜亂無章有直接的關系。
弘光時期,四川作為“寇亂重災區”,官員的任命還是比較有章法的,主要有三位:
“壹號首長”王應熊,字非熊,四川巴縣(今重慶巴南區)人,萬歷四十壹年(1613年)進士。弘光建政後,王應熊被委任為兵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,總督川、湖、雲、貴軍務,專辦“川寇”。孫可望占領遵義時,王應熊躲進山區,於永歷元年(1647年)病逝。
“二號首長”樊壹蘅,字君帶,四川敘州人,萬歷四十七年(1619年)進士。弘光時期被任命為總督川、陜軍務,跟隨王應熊“剿賊”。
“三號首長”馬乾,任四川巡撫,在與入川的清軍作戰中陣亡。
弘光時期的“三巨頭”死了倆,領導班子需要重新組建。永歷朝廷這壹“重組”,徹底亂套了,主要官員的任命如下:
樊壹蘅留任川陜總督。
調偏沅巡撫李乾德任川東北巡撫,不久升任總督。
朱容藩任總督川東軍務。
楊喬然、江而文任巡撫,楊不久升任總督。
詹天顏任川北巡撫。
範文光任川南巡撫。
——糊塗了吧?其實所有人都糊塗!
總督、巡撫這樣的高級官員本該“壹個蘿蔔壹個坑”,結果卻是“壹抓壹大把”,麻煩很快就出現了:聽誰指揮?
名義上歸樊壹蘅統壹指揮,但同為“總督”的李乾德、朱容藩、楊喬然根本不買他的賬,樊壹蘅“無所施節制,但保敘州壹郡而已”,混得比清軍的四川巡撫李國英還要慘。人家雖然也只守著保寧壹府,但好歹說話有人聽,樊壹蘅卻只能“自產自銷”。
李乾德、朱容藩、楊喬然不買樊壹蘅的賬,相互之間也不買賬,下面的巡撫更別提了,全都“各自署置,官多於民”。反正四川軍閥多,靠著壹個是壹個。官帽頂個屁用,全憑槍桿子說話!
各懷鬼胎的朝廷官員,加上擁兵自重的軍閥,整個四川豈止是壹鍋粥,簡直就是壹團亂麻!
福建的亂局,主要表現在“浙系”、“閩系”、“地方系”幾大派系互不買賬、各自為戰,而四川的亂局,除了派系更多、協調更難以外,還有更致命的壹條:抗清的沒有,打內戰大大的有!
從永歷二年(1648年)至永歷三年(1649年),四川內戰頻發,規模比較大的就有四場。
第壹場內戰是楊展、馬應試、王祥之間的“川南會戰”。
王祥盤踞在遵義、江津壹帶,大肆盤剝地方,搞得民不聊生。永歷二年(1648年)初,有人唆使時任四川巡按禦史的錢邦芑,向實力比較雄厚的楊展求援,請他出兵川南“替天行道”、“伸張正義”。
錢邦芑做了多年的禦史,早就養成了嫉惡如仇的“職業病”。聽說王祥在遵義胡作非為,錢邦芑經不住忽悠,果然拍案而起,給楊展寫了壹封求援信。
楊展也是“憤青”壹個,看到錢邦芑的書信,立即決定率師出征,要給王祥壹點顏色看看。
但是,想打王祥並不容易,因為從川西的嘉定到川南的遵義,瀘州是必經之地,而盤踞於此的馬應試不讓道。
好狗不擋道,除非妳欠扁。
楊展不管三七二十壹,對著瀘州的馬應試壹頓狠揍。王祥開始還不知道怎麽回事,正躲在遵義看熱鬧,很快就得知楊展其實是沖著自己來的。——這還了得!妳楊展活得不耐煩了?
王祥果斷率軍出擊,聯合馬應試把楊展給收拾了壹頓。楊展帶來的兵力不多,而且強龍難壓地頭蛇,大敗而歸。
第二場內戰是“川貴之戰”,也是因王祥而起,而且索性打出四川,跟貴州的皮熊幹上了。
遵義距離貴陽不算太遠,中間隔著壹條烏江,王祥壹直都想把實力稍弱的皮熊壹口吃掉。永歷二年(1648年)七月,王祥趁皮熊不備,揮師南下渡過烏江,壹舉包圍貴陽。皮熊被困在貴陽挨揍,貴州將領武邦賢、楊光謙看不下去了,於次月率兵支援,給皮熊解了圍,王祥率部撤回烏江。
皮熊哪裏咽得下這口氣,經短暫準備後,便於十月北上烏江,給王祥來了壹個“以牙還牙”。此後,兩人便在烏江兩岸妳來我往、沖突不斷。由於雙方實力相當,誰也吃不了誰,皮熊、王祥終於在年底決定停火,握手言和。
“川南會戰”和“川貴之戰”都屬於局部性質的軍閥混戰,除了參戰各方有所損失以外,後果還不算太嚴重。接下來的第三場內戰,鬧騰得就比較厲害了,這就是發生在川東地區的“朱容藩之亂”。
朱容藩是楚王朱楨(朱元璋第六子)的遠支後裔,屬於皇親中的“邊緣人物”。張獻忠攻陷武昌的楚王府後,僥幸逃脫的朱容藩開始浪跡天涯,打著“郡王”的旗號四處招搖撞騙。
幾年來,他先後騙過左良玉、馬士英和大順軍,但是都沒有成功,最後總算騙過了丁魁楚,推薦給永歷朝廷,朱由榔安排他執掌宗人府。
宗人府是管皇家事務的,算得上是美差了。可如今兵荒馬亂,皇親死的死、逃的逃,這種差事實在沒有什麽前途。
壹心想出人頭地的朱容藩很快就發現了契機——處於“權力真空”的四川!
朱容藩主動請纓,被朝廷委任為總督川東軍務,取道湘西的辰州抵達湖北施州衛(今湖北恩施),與流落到此的鄖陽守將王光興碰個正著。
來到施州後,朱容藩重操舊業,打起了“楚王世子、天下兵馬副元帥”的旗號,繼續在川東、鄂西地區招搖撞騙。
朱容藩的鬼把戲還真迷惑了壹些人,除了被清軍打得暈頭轉向的王光興以外,於大海、李占春也深信不疑,老老實實地服從朱容藩的號令。
永歷元年(1647年)夏,清軍涪州總兵盧光祖攜搶掠而來的財物、女子,由重慶順江而下,妄圖打通川鄂水道。朱容藩命令於大海、李占春率部果斷攔截,於七月十壹日在忠州大敗盧光祖,清軍殘部退回保寧。
初戰告捷,朱容藩的膽識愈壯。趁著清軍收縮防線,朱容藩帶著受蒙蔽的王光興、李占春、於大海等部,壹面在川東、川南地區“收復”失地,壹面繼續招搖撞騙,忽悠“三譚”、馬應試、楊展,還有“搖黃十三家”中的呼九思、景可勤等歸附自己。
隨著勢力不斷壯大,朱容藩的野心也急劇膨脹。永歷三年(1649年)二月,羽翼漸豐的朱容藩改忠州為“木定府”,堂而皇之地在川東做起了“楚監國”,公然“另立中央”。
朱容藩“自立”,支持的都是被忽悠的,反對的都是不信邪的,而且大有人在。李乾德、袁韜堅決反對,並擊潰了朱容藩派來“清剿”的李占春部。
“憤青”錢邦芑也堅決反對,雖然沒有槍桿子,但他有筆桿子。錢邦芑趕緊向朝廷上疏,又將告狀的疏稿傳閱四川、湘西、鄂西,揭露朱容藩的本來面目。
朱容藩的運氣確實太差,堵胤錫、馬進忠此時正好撤到施州衛休整。得知這個驚天消息,堵胤錫立即派人前往夔州質詢朱容藩:妳說說看,這到底是怎麽回事?
見到堵胤錫的使者,心虛的朱容藩百般狡辯,卻漏洞百出,李占春、於大海、王光興這才恍然大悟,知道自己上了這個“江湖騙子”的當。但是,朱容藩畢竟是皇親,使者也不是朝廷派來的。朝廷沒表態,大家還真拿這個騙子沒辦法。
不過,朱容藩在夔州、忠州是待不下去了。三月,“朱騙子”卷起鋪蓋,移駐萬縣,重金籠絡“搖黃十三家”中的白蛟龍、楊秉胤部作為貼身護衛,又聯絡“三譚”做了靠山,妄圖有朝壹日“東山再起”。
七月,朱容藩手又癢癢了,率部進攻石柱土司。土司向李占春、於大海求援,“受騙者”終於找到收拾“朱騙子”的理由了!
李占春、於大海果斷率部救援,二十五日大敗朱容藩的軍隊,活捉白蛟龍,譚文逃回萬縣,“朱騙子”落荒而逃,最後在雲陽被追兵擒殺。
在永歷朝廷任命的四川官員中,除了“騙子”朱容藩犯上作亂以外,時任川東北巡撫的李乾德也不是什麽好鳥。
“朱容藩之亂”被鎮壓前後,李乾德親自導演了四川的第四場內戰——“川南大火並”。
永歷三年(1649年)初,“搖黃十三家”中的袁韜部“轉戰”到了川南的富順。七月,作為川東北巡撫的李乾德也來到富順。除此之外,原陜西裨將武大定、“搖黃十三家”的呼九思部也先後投奔袁韜。
壹群人聚在富順,雖然身份不同、來路不同,但都有壹個共同點:沒飯吃!(俱絕糧,餓死者甚眾。)
李乾德不愧是朝廷官員,腦子比較靈活,立即給大家出了壹個主意:找四川的“大財主”楊展要!(唯求救於楊展,展若從即無饑乏患矣。)
楊展倒是願意扶貧濟困,但李乾德得寸進尺,又提出了壹個無理要求:讓楊展交出財政大權。
楊展徹底怒了:憑什麽?有本事來搶!
七月二十九日,李乾德與袁韜、武大定合謀(呼九思不久前病死),以袁韜生日為名,擺了壹出“鴻門宴”,將前來赴宴的楊展擒殺,隨即率軍突襲嘉定。
貪戀錢財的李乾德謀害了實力雄厚的楊展,令四川各路軍閥十分寒心。李占春引兵來援,但打不過袁韜,只能悻悻而去。空有總督頭銜的樊壹蘅也看不下去了,寫信斥責李乾德:“背施忘好,而取人杯酒之間,天下其謂我何?”
李乾德不僅置之不理,還將這種卑劣的行徑自詡為“救時大計”,率袁韜、武大定繼續猛攻嘉定,以達到斬草除根的目的。
十二月二十四日,嘉定失守,楊展長子楊璟新率殘部逃往保寧,並於次年正月十六日向清軍投降。
四川痛失最強大的壹股抗清勢力,“自是蜀事大壞矣”。
入川清障
四川亂成這副鳥樣,永歷政權作為名義上的中央,既鞭長莫及,又自顧不暇,只有隨他們瞎折騰。
永歷朝廷全當沒看見,可孫可望看不下去了:妳們精力這麽旺盛,不去抗清也就算了,別擋道啊!
攘外必先安內,抗清必先“清障”,孫可望決定先易後難、殺雞給猴看。
早在永歷三年(1649年)八月,孫可望就派部將白文選率部前往貴州安順,探查皮熊的虛實。永歷四年(1650年)四月,李定國、劉文秀率大軍占領貴陽,以武力逼迫貴州軍閥皮熊、貴州巡撫範鑛“結盟”。皮熊不敢硬頂,只好退守平越(今貴州福泉)伺機而動。
八月,孫可望決定親自趕赴貴陽。平越的皮熊和遵義的王祥都心虛,趕緊給孫可望“表忠心”:咱們都挺聽話的,您老人家就不用親自跑壹趟了。
孫可望哪這麽容易忽悠,根本就不搭理這倆老油條,執意前往貴陽,並派部將馮雙禮、王自奇進攻平越,活捉皮熊。九月,劉文秀、白文選率軍進抵川南的遵義、永寧,逼迫王祥、侯天錫歸附。年底,孫可望的軍隊占領銅仁,整個貴州和川南地區已經納入孫可望的控制範圍。
孫可望的大動作,有效地震懾了只會“窩裏鬥”的四川各路軍閥。在進軍川南、掃蕩貴州的同時,孫可望又與永歷政權在四川名義上的最高長官——川陜總督樊壹蘅取得聯系。樊壹蘅早就想結束亂局,只是苦於無權無兵。
形勢所迫,只談合作。樊壹蘅沒有瞿式耜那麽多“講究”(其實就是階級成見),管妳是大西軍還是大順軍,誰能摁住四川這群刺頭,就跟誰合作!
在樊壹蘅的號召下,大部分四川軍閥“深明大義”,爭先恐後地表示聽從指揮、結束內戰、壹致對外,其實主要是怕被收拾。
在這個世界上,有貪生怕死的,也有豁得出去的。盡管四川的大多數軍閥都歸附了孫可望,但也不乏伸長脖子硬頂的。
李乾德就是壹個脖子硬的。自從導演了“川南大火並”,李乾德帶著袁韜、武大定攫取楊展在嘉定、峨眉地區積累的財富,發了壹筆橫財,也有了跟孫可望對著幹的資本。
樊壹蘅在四川本來就是壹個“光桿司令”,李乾德就是最大的刺頭。暗殺楊展之後,樊總督親自寫信斥責身為川東北巡撫的李乾德,李巡撫曾對樊總督極其鄙視,公然叫囂“救時大計,詎豎儒可知”。樊總督號召各路軍閥“軍令政令統壹”,也就是聽孫可望指揮,李乾德最先跳出來反對。不久後,樊壹蘅病死,李乾德跳得更高,公然以四川最高長官自居。這倒是給壹直想染指四川的孫可望幫了大忙:正愁找不到借口,這回妥了,咱給楊展報仇去!
李乾德級別最高、反對最堅決,所以也最先挨揍。永歷五年(1651年),孫可望作出了分兩路進軍四川的作戰部署,劉文秀率主力渡金沙江,取道建昌(今四川西昌)入川,王自奇部則取道畢節、永寧,奪取川南。
面對孫可望大軍壓境,李乾德決定死扛到底,派武大定率主力前往雅州(今四川雅安)迎戰,另派出壹部兵力駐防敘州。
八月,劉文秀在滎經全殲了武大定的精銳部隊張林秀部,武大定連滾帶爬逃回嘉定,與在嘉定坐鎮的李乾德、袁韜抱頭痛哭壹番之後共同抱頭鼠竄。劉文秀窮追不舍,李乾德、袁韜攜帶的財物太多,走得很慢,終於在仁壽被劉文秀的追兵活捉,武大定落荒而逃。
劉文秀接到的是“斬草除根”的死命令,壹個都不能放跑。如今武大定跑了,但他的兒子武國治跟袁韜在壹起,落到了劉文秀的手裏。劉文秀通過武國治向武大定傳達了“首犯必辦,脅從不問”的寬大政策,已經走投無路又有兒子捏在別人手裏的武大定決定試試運氣,回來“自首”。
事實證明,劉文秀說話是算數的。袁韜、武大定都得到了寬大處理,只有李乾德和弟弟李九德被羈押,送往貴陽治罪。李乾德深知孫可望不會放過自己,與其死得難看,不如自己了斷。押解至犍為境內時,李乾德、李九德趁看守疏忽,投水自盡,好歹留個全屍。
另壹路入川的部隊——王自奇部進展也比較順利,占領永寧後繼續向遵義推進。九月,王自奇將“結盟”以後不怎麽老實的王祥消滅,川南全面平定。
劉文秀做完川西的“善後”,隨即率軍順江東下,聯絡川東武裝,賀珍、王光興、張堯翠等部紛紛與孫可望結盟,宣布“服從領導”。
除了李乾德以外,四川還有壹路軍閥拒絕與孫可望合作——盤踞涪州、長壽地區的李占春、於大海部。
李乾德不合作是因為狂妄自大、貪戀權財,李占春、於大海則另有隱情。孫可望率大西軍余部從西充南下時,在重慶幹掉了南明軍的守將曾英。李占春、於大海正是曾英的“義子”,他們拒絕與“殺父仇人”合作。
在孫可望看來,不管什麽原因,只要抗拒改編,都是欠收拾。劉文秀在收拾李乾德、袁韜的同時,也派出部將盧明臣率軍清剿川東南。李占春、於大海當初想替楊展報仇,結果被李乾德壹頓痛扁。連李乾德、袁韜都揍不過,更別提劉文秀了。
果然,李占春、於大海比李乾德、袁韜死得還要快,七月份就被盧明臣打得四處亂竄。眼看四川已經待不下去了,李占春、於大海向東撤退,準備前往湖北投降清軍。
軍閥想在四川立足很難,但想出川投降也不是壹件容易的事。李占春、於大海的三萬殘軍走到半道上,便遭遇夔東武裝的壹路截殺。夔東地區形勢復雜,山頭眾多,但各路“山大王”如今只有壹個目標:痛打落水狗!
李占春、於大海成了過街老鼠、眾矢之的,壹路損兵折將,跌跌撞撞向湖北靠近,終於在十壹月十壹日抵達清軍的防區。
安全是安全了,但日子不見得好過。清軍荊州總兵鄭四維將前來“投誠”的李占春、於大海部安排在松滋百裏洲休整,接下來的手法跟何騰蛟、瞿式耜如出壹轍:要錢沒有,要糧不給!肚子餓?自己想辦法!
這壹招術相當無恥,卻屢試不爽。當初,田見秀被何騰蛟用這招逼得拍屁股走人,郝搖旗也被瞿式耜逼得四處抓狂。輪到李占春“中招”的時候,麻煩大了。
跑?壹個叛徒,能往哪兒跑?
搶?清軍正愁沒借口收拾妳,莫非嫌命長?
跑不能跑,搶不能搶,李占春終於“看破紅塵”、皈依佛門。——看來,只要逼到沒法活,方法總比問題多!
李占春出家,正中鄭四維的下懷。
其實,鄭四維搞這個把戲的動機,跟何騰蛟、瞿式耜是有本質上的區別的。南明的大臣出於個人利益和階級成見,不惜自毀長城,而鄭四維是想廢掉這支軍閥部隊的武功。
老大出了家,雖然還有個於大海,但基本上已經是群龍無首、人心惶惶,不久便自動瓦解。達到目的後,清軍又招撫李占春“還俗”,先後出任安陸副將、黃州總兵等職,彰顯自己的“博大胸懷”。
劉文秀、王自奇的軍隊在四川大打出手,將李乾德、王祥、李占春幾大軍閥勢力揍得滿地找牙,有效地震懾了其他軍閥。
無論當初表態願意“結盟”的軍閥是出自真心還是假意,如今都死心塌地了。特別是夔東地區的軍閥武裝,親眼見證了李占春、於大海的悲慘境地,紛紛“扼險自守,差人申好”。至此,“三川之阻兵皆盡”,四川(只有保寧仍由清軍控制)、貴州已在孫可望的掌控之中。
抗清的道路通暢了,但孫可望並沒有貿然進軍,因為拿下四川和貴州以後,孫可望的麻煩更大。
——四川和貴州都是吃了上頓沒下頓,好容易有個自給有余的楊展,偏偏又被李乾德給剁了,僅憑雲南壹省之力怎麽養得活?
——大軍出去抗清,後勤補給怎麽保證?有沒有糧食倒是其次,就算有糧食,怎麽穿過四川、貴州送過去?那裏到處都是餓紅了眼的饑民啊!
以前四川、貴州是別人的地盤,孫可望全當看不見。如今兩副爛攤子落到自己的手裏,孫可望終於見識到沒有最爛、只有更爛了。——我說豪格追到遵義怎麽突然放我壹馬,原來這爛攤子簡直是爛得令人發指!
攤子再爛,孫可望也只能埋頭苦修,因為不把四川、貴州的攤子修好,孫可望根本就走不出去。不能走出去發展,三十多萬大軍遲早要被困死在雲南。
貴州涅槃
“流賊”出身的孫可望品行不咋地,既自私又貪權,最後還投降了清軍,但不應該因為這些劣跡而抹殺他在西南的“政績”。
雲南在孫可望的手裏,不出三年便呈現出壹片太平景象。控制四川、貴州之後,孫可望又大力推廣“雲南經驗”。特別是在向來貧瘠的貴州,孫可望確實下了很大的功夫,比較大的措施主要有四個方面:
其壹,統壹軍令政令。
皮熊被活捉後,分散在貴州各地的殘余勢力退守山區、負隅頑抗。除此之外,各地土司也“占山為王”,以前與皮熊抗衡,現在又與孫可望抗衡。凡是外鄉人,他們壹概不鳥。
孫可望派白文選鎮守貴陽後,便開始對南明軍殘余的散兵遊勇、各路山匪進行收編,凡是抗拒收編者壹律清剿,終結了大小軍閥占山為王、殘害百姓的亂局。
其二,裁撤冗員、整頓吏治。
貴州作為南明的屬地,也有官員多如牛毛、官場魚龍混雜的通病,最後的結果都是政府烏煙瘴氣,百姓不堪重負。針對這種狀況,孫可望首先將官員“過篩子”,挨個開展“政審”和清查,欺壓百姓的直接剁掉(戮奸蠹民者),並對南明政權胡亂任命的大量冗員進行裁撤。
篩剩下的官員也別忙著彈冠相慶,因為日子不見得好過。孫可望規定:“凡官員犯法,重則斬首、剝皮,輕者捆打數十,仍令復任管事。”
孫可望不是嚇唬嚇唬,而是動了真格,接下來的這個場景也屢見不鮮:
某官員正端坐堂上審案,對嫌疑犯用刑逼供。此時,突然闖進來壹幫人宣讀“上峰指令”,說某官員犯某某罪,依律杖二十。於是,正趴著受刑的嫌疑犯被拎到壹邊,堂上的官員被拽下來趴上去。打完二十棍,官員、嫌疑犯各歸其位,該審案的審案,該受刑的受刑,就當什麽都沒有發生過。
其三,招徠商賈,安撫百姓,恢復經濟生產。
貴州是喀斯特地貌的山區,找塊跟足球場壹般大的平地基本上不可能,而且石多土少。由於自然環境惡劣,貴州歷來土地貧瘠,交通不便,耕作方式原始(牛都沒法用),再加上軍閥皮熊的大肆盤剝,即便是極其落後封閉的自然經濟也瀕臨崩潰。
在這種情況下,孫可望壹面招徠商賈、恢復貿易,壹面采取“休養生息”的政策,又派軍隊就地組織開荒,“安撫遺黎,大興屯田”,積極恢復農業生產。
其四,發展交通,積極備戰。
李白經劍門關入川,曾留下“蜀道難,難於上青天”的名句。王陽明被流放貴州龍場驛(今貴州修文)時,更有“嘆峰際連天兮,飛鳥不通”的感慨。可以說,“黔道難”比起“蜀道難”,有過之而無不及。
交通,不僅關系到出兵問題,而且直接決定後勤補給能力。“要致富,先修路”是現在的口號,對於孫可望而言,確切的說法是“要打仗,先修路”。
於是,“孫國主”成了“孫總工”,大張旗鼓地開始修路,遇山開道,遇水架橋,貴州的交通狀況得到極大的改善。
道路暢通,既方便了自己,也方便了敵人,孫可望又實行“路印”制度,嚴防清軍間諜趁機混入。
在孫可望的治理下,昔日民不聊生的貴州猶如鳳凰涅槃,初步呈現出壹片欣欣向榮。根據史料記載,貴州“官絕貪汙饋送之弊,民無盜賊攘奪之端”,雖然不免有些誇張,但經濟得到較快的發展卻是不爭的事實。
孫可望治理貴州,主要是為了壯大自己的實力。因此,貴州經濟得到恢復之後,稅賦是相當繁重的。
俗話說“兔子不吃窩邊草”,作為孫可望的老巢,雲南的稅賦是“官壹民九”,達到了全國的最低點。但對於貴州,孫可望可就沒這麽客氣了,稅賦壹般都在五成以上,部分地區甚至達到九成。在孫可望的橫征暴斂下,元氣稍有恢復的貴州再壹次遭受無情的摧殘,為後來清軍順利通過貴州進入雲南清剿,奠定了堅實的“群眾基礎”。
以後的事情以後再說,就目前來看,孫可望還是比較滋潤的。
天無絕人之路
“朱門酒肉臭,路有凍死骨”,當孫可望在西南風生水起的時候,南寧的忠貞營卻在苦苦求生。
自打從湖南敗退入兩廣,沒了堵胤錫的庇護,寄人籬下的忠貞營便開始江河日下。幫陳邦傅打下南寧,陳邦傅不僅不酬謝,還千方百計地想把忠貞營擠走。李錦病死後,高壹功曾率部挺進廣東,幫永歷朝廷抗清,卻屢遭嚴起恒、李元胤、金堡等頑固派的刁難排擠,無功而返。
至永歷四年(1650年)下半年,忠貞營在兩廣已經無法立足,高壹功、李來亨決定轉移。
作決定不難,麻煩的是該往哪裏走。
高壹功、李來亨將地圖壹攤開,發現道路雖然遍布天下,但沒有壹條能讓忠貞營順暢通過。
東面,尚可喜、耿繼茂大軍正在絞殺廣州,永歷朝廷又抵制忠貞營摻和,忠貞營也不想再傻啦吧唧地當炮灰了。
北面,孔有德大軍正在湖南修“爛尾樓”,忠貞營趕過去,正好夠孔有德壹頓午飯。
西面,孫可望的地盤更麻煩,雖然大西軍、大順軍都是農民軍,但張獻忠跟李自成壹直不對付,恩怨由來已久,還曾經為爭奪四川大動幹戈。舊債未了又添新賬,高壹功反對孫可望封王時相當積極。在這種情況下,投奔孫可望,還不如原地待著,受的窩囊氣還少些。
南面,壹片汪洋。
形勢就是這麽壹個形勢,往哪兒走都是送死,忠貞營想討個全屍,似乎只有向南投奔龍王了。
天無絕人之路,只有絕路之人!
思來想去,高壹功、李來亨決定冒壹次險:北出廣西,穿過孔有德、孫可望之間的湘西,進入夔東山區發展。
永歷四年(1650年)十二月,高壹功、李來亨率忠貞營從南寧出發,帶著輜重、家眷,浩浩蕩蕩向北而去。由於擔心受到襲擊,忠貞營不敢走大路,而是選擇崎嶇小道艱難跋涉。
次年,忠貞營按既定路線經過湘西保靖時,遭遇已投降清軍的土司彭國柱襲擊,高壹功中毒箭身亡。臨危受命的李來亨率部突圍,歷盡千辛萬苦,終於率領殘部抵達夔東,與活動在該地區的抗清勢力會合。
抵達目的地後,對永歷政權切齒痛恨的李來亨毅然取消忠貞營的番號,成為夔東山區的“單幹戶”之壹。
隨著忠貞營的“加盟”,過去的“搖黃十三家”逐漸演變成了“夔東十三家”,在川東、鄂西地區利用地理優勢繼續堅持抗清鬥爭。
敬鬼神而遠之
永歷政權將忠貞營逼入絕境,而“逃跑帝”朱由榔自己的日子也不比高壹功、李來亨好過多少。
廣西省會桂林、廣東省會廣州相繼失守,朱由榔逃到南寧避難。但是,清軍此次決心蕩平兩廣,南寧雖然深居廣西內地,也絕非安身之所。
萬不得已之下,朱由榔不得不放下臉面,將最後的希望放到了孫可望的身上。問題在於,朱由榔可以有希望,但孫可望是否接招就得兩說了,畢竟永歷朝廷在“請封之爭”上做得實在太絕。
“逃跑帝”想依靠孫可望“東山再起”(其實就是為了茍延殘喘),“請封”的問題是繞不過去的。由於永歷朝廷已經走投無路,急紅了眼的朱由榔相當果斷:封孫可望為冀王,不爭論!
朱由榔認為自己做了最大的讓步(封“壹字王”),但孫可望依然不改初衷:要麽“秦王”,要麽免談!上次孫可望有所妥協,提出“要敕不要印”的折中方案,這壹次卻坐地起價,敕書、大印壹個都不能少。熱臉貼了冷屁股,朱由榔覺得丟不起這個人,又沒談成。
永歷五年(1651年)二月,孔有德的清軍自柳州南下,揮師直指南寧。逃無可逃的朱由榔急眼了,孫可望比他還要急眼:如果這塊金字招牌沒了,自己這只“潛力股”立馬跌停。
形勢危急,孫可望決定投桃報李,給永歷朝廷送來壹張熱臉——派賀九儀、張明誌率五千精兵協防南寧。
別看孔有德人多勢眾,還真不壹定幹得過裝備精良、訓練有素、以逸待勞的五千精兵,孫可望對此胸有成竹。
孫可望不是活雷鋒,五千精兵也不是“保護”永歷朝廷的“誌願者”。賀九儀、張明誌進入南寧後,主要幹了三件事:
其壹,布置南寧城防,抵禦可能進犯的清軍。
其二,對“請封之爭”中的“頑固勢力”反攻倒算,殺死兵部尚書楊鼎和,逼死大學士嚴起恒,向朱由榔示威。
其三,為孫可望請封“秦王”。
撞破南墻始回頭,見到棺材方落淚,朱由榔終於屈服了。如今,南寧在別人的手裏,兩只“死雞”擺在自己面前,朱由榔實在找不到拒絕的底氣。
三月,永歷朝廷正式冊封孫可望為“秦王”,歷時兩年的“請封之爭”總算是塵埃落定。
孫可望如願以償,但並沒有給朱由榔好臉色。對於孫可望而言,永歷朝廷和朱由榔,不過是招搖過市的幌子、壯大實力的招牌。貼壹張熱臉,孫可望不是為了給自己找個大爺。朱由榔倒是好對付,只會在朝堂上唧唧喳喳的大臣才是大麻煩。
因此,孫可望對待永歷朝廷和朱由榔,始終奉行壹條基本原則:“敬鬼神而遠之。”——控制朝廷是必須的,但廷臣想唧唧歪歪,免談!
既想“敬”又要“遠”,思維很獨到,但問題是不太現實。馬士英、鄭芝龍想做到,但都沒能做到,他們把持朝政的同時,也飽受群臣的攻訐。這個看似無解的“夢想”,到了孫可望這裏,神話成了現實。
孫可望得到“秦王”的冊封,宣布效忠朱由榔,接著只做了壹件事:在貴陽建立行營六部(相當於“臨時中央”),以自己的親信充任各部尚書。
朱由榔帶著為數不多的大臣留在南寧,孫可望並沒有讓他們搬家的意思。於是,貴陽的“臨時中央”實際上取代了南寧的“正式中央”,朱由榔還是朱由榔,不過不再是權臣手中的“傀儡”,而是神龕上的“牌位”。
孫可望為了權力不擇手段,但楊畏知是個厚道人。奉命前往南寧時,楊畏知實在看不慣賀九儀、張明誌在這裏狗仗人勢,奮筆上疏彈劾。
看到楊畏知的奏疏,朱由榔眼淚嘩嘩的:千金易得,知己難尋,終於有人肯說句公道話了!朱由榔雖然不敢拿賀九儀、張明誌怎麽樣,但提拔楊畏知入閣還是可以的。
很多時候,講公道、說真話是要付出代價的。
在朱由榔看來,褒獎楊畏知,是在跟孫可望套近乎。但對權力極其敏感的孫可望不這麽看,他認定楊畏知背叛了自己。是在“賣主求榮”。
永歷五年(1651年)五月,楊畏知被孫可望派人押回貴陽處死。——這就是楊畏知說句公道話的代價,但孫可望未必是真正的贏家。既然永歷政權威信掃地,孫可望又能身價幾何?出來混遲早要還,孫可望當然也會付出代價,只是需要壹點時間而已。
此時的孫可望小人得誌、趾高氣昂,“逃跑帝”朱由榔卻是如履薄冰、膽戰心驚。十壹月,朱由榔最不想看到的壹幕終於發生了——孔有德大軍逼近南寧。
賀九儀、張明誌的五千精兵是否願意防守南寧、是否有能力守住,應該都不是問題,畢竟孫可望並不希望這塊“金字招牌”落入清軍之手。問題在於,朱由榔根本就不是固守的性格。
老大坐鎮指揮、鼓舞士氣,將來犯的清軍打得抱頭鼠竄。——朱聿鍵會這樣做,但對於靠逃跑過日子的朱由榔而言,無異於“逆天”!
打不贏要跑,打得贏也要跑,這才對得起“逃跑帝”的名望。可是,這壹回咱們往哪兒跑?
就當前的形勢來看,朱由榔有三個選擇:
其壹,向海上逃亡,投靠福建沿海的鄭成功部。
不靠譜!
鄭成功雖然口頭上奉永歷為正朔,但大難臨頭是否會接收這位爺?——不壹定!
即便鄭成功肯“收容”,他會不會步鄭芝龍、孫可望的後塵?——很有可能!
做傀儡倒還在其次,可鄭成功自己都饑寒交迫、漂泊不定,朱由榔能跟著混多久?
總之,風險太大!
其二,向南逃往越南避難。
更不靠譜!
越南是明朝的屬國,什麽是屬國?有奶便認娘,強悍便認爹!妳信不信,只要朱由榔邁出國門,越南王立即就能將他五花大綁,“遣返”給孔有德,做歸附清朝的“投名狀”。
其三,向西進入孫可望的地盤。
相對而言,這個選擇稍微靠譜壹點,孫可望也早在五月就提出移蹕雲南的動議,但朱由榔壹萬個不願意。孫可望是什麽人,他不是沒見識過。寄人籬下的生活,用腳趾頭都能想到該會有多丟人、多悲慘。
朱由榔“不欲就可望”,但很多事情不是他說了算的。朝議之中,三種選擇都有人提了,接著輪到首輔吳貞毓拍板。其實,這板根本沒必要拍。地球人都知道,永歷朝廷除了歸附孫可望,已經別無選擇。但是,吳首輔曾經跟隨嚴起恒極力反對孫可望封王,嚴起恒、楊鼎和屍骨未寒,擔心“拉清單”的吳首輔實在不敢拍這個板。
“搬家”問題久拖不決,賀九儀怒了:不去拉倒,妳們愛上哪兒上哪兒,我不管了!
賀九儀帶著五千精兵跟永歷朝廷“拜拜”,朱由榔急了:還討論個屁,跑啊!
往哪兒跑?——還能往哪兒跑?有選擇余地嗎?
十二月初,朱由榔乘船倉皇逃離南寧,溯左江至瀨湍(今廣西崇左附近)。上遊水太淺,船沒法再繼續走,朱由榔壹行人棄舟登岸,經龍英(今廣西大新附近)、歸順(今廣西靖西)、鎮安(今廣西德保),向雲南進發。
清軍窮追不舍,跑得賊快的朱由榔第壹次逃跑得如此膽戰心驚,所幸在桂、滇邊境與前來“迎駕”的狄三品、高文貴、黑邦俊部撞個正著。雖然驚魂未定,但此次提心吊膽的歷程總算終結了。
永歷六年(1652年)正月初壹,朱由榔在雲南邊境的壹個小山村裏過了壹個慘兮兮的新年。朱由榔不知道,接下來該去哪裏,確切地說,將會被孫可望安排到哪裏去。
強顏歡笑過完年,朱由榔在“迎駕”部隊的帶領下,繼續艱難跋涉,半個月後抵達廣南府。憑心而論,朱由榔並不想去昆明或者貴陽,天天看著孫可望的臉色過日子。他想就此留在廣南,舒舒坦坦了此殘生。
朱由榔的想法,孫可望壹般都不會支持,他不希望永歷朝廷賴在廣南不走。既然是“敬鬼神而遠之”,廣南府似乎還不算遠。當然,這話不能明說,冠冕堂皇的理由是:廣南靠近邊境,不可預知的風險較大。(廣南雖雲內地,界鄰交趾,尚恐敵情叵測。)
廣南不能住,昆明、貴陽更別提了,朱由榔不想去,孫可望更不讓去。那麽,永歷朝廷往哪裏擺?孫可望物色了壹個相當遙遠的“風水寶地”——貴州安隆千戶所,朱由榔駐蹕後改為安龍府。
遙遠,有時候不單指空間上的距離。安龍的遙遠,超乎所有人的想象。
安龍位於貴州、雲南、廣西三省交界處,原是隸屬貴州都指揮司的“千戶所”,屬於屯兵機構。這座位於大山深處、居民只有百余戶的所城,地域相當狹小,十分鐘便能繞著城走壹圈。(所城圍壹裏二百七十步。)
從南寧到廣南,再到落腳安龍,朱由榔只有壹個感覺:距離“九五之尊”越來越遠。這哪裏是移蹕,簡直就是落草!
永歷朝廷自己沒本事,將地盤丟個精光,淪落到寄人籬下的地步,確實也沒底氣講什麽條件,只有“客隨主便”。二月初六,朱由榔帶著五十余文武大臣、三千兵丁家眷,步履蹣跚抵達安龍。
壹無所有的朱由榔,真正過上了“孤家寡人”的悲慘生活。(王自入黔,無尺土壹民。)
孫可望決定不鳥朱由榔,自封為“國主”甩開膀子單幹。在白文選、王尚禮、王自奇等親信的支持下,孫可望以微弱的優勢暫時摁下了李定國、劉文秀,漸成“壹家獨大”之勢。
不過,出滇抗清不是壹件容易的事情,孫可望的實力是有的,但面臨壹個很現實的問題:怎麽去?
廢話!那時候又沒有飛機,當然得走過去。——既然不能飛過去,麻煩就大了!
雲南地處西南壹隅,從這裏出兵抗清有兩條路:壹是東出貴州,進入湖南;二是北抵金沙江,順流穿過四川,進入湖北。但是,貴州、四川名義上服從永歷政權的領導,並不是孫可望的地盤。
——他們會給孫可望讓道嗎?
——即便同意借道,他們是否會趁虛而入,搗掉孫可望在雲南的老巢?
對於決心出兵抗清的孫可望而言,“攘外必先安內”既非托辭,也不是空話。盤踞在四川、貴州的這群鳥人,自己不抗清,還擋著別人抗清的路。不解決掉貴州、四川的問題,這仗根本沒法打!
貴州地域狹小,軍閥勢力也比較單壹。偏橋(今貴州施秉)總兵皮熊趁著孫可望率軍入滇,帶著壹群烏合之眾賴在貴陽做“土霸王”,僅此而已。就他那副“熊樣”,孫可望擡起壹腳就能踹死三回,不足為慮。
真正的麻煩在四川,這裏不僅地域廣闊,而且各種勢力犬牙交錯,比“浙系”、“閩系”、“地方系”攪和下的福建還要混亂好幾倍!
前面說過,豪格、吳三桂大軍壹路追擊孫可望,追到遵義府就追不下去了。由於肚子餓,決定班師回朝,只留下王遵坦、李國英鎮守四川,這是永歷元年(1647年)的事情。
清軍留守部隊兵力單薄,王遵坦、李國英當然不能遍地“撒豆子”,那樣只會被南明、大西以及當地的殘余勢力各個擊破。因此,清軍名義上駐守四川,實際上絕大部分軍隊都龜縮在川北的保寧府(今四川閬中)附近。這年十壹月,被委任為四川巡撫的王遵坦病死,由李國英繼任,依然將主力駐守在保寧,並不敢輕舉妄動。
除了保寧府屬於清軍控制以外,四川各地就比較熱鬧了,光是數得上號的就有七股軍閥勢力。
——川西有壹股,也是實力最強的,即盤踞嘉定(今四川樂山)、峨眉壹帶的楊展部。
楊展,四川嘉定人,崇禎十二年武進士,曾任明軍參將,大西軍入川後被俘。僥幸逃脫後,楊展在敘州(今四川宜賓)壹帶組織軍隊抵抗。隆武二年(1646)進抵嘉定、峨眉壹帶建立根據地,致力於恢復生產、發展經濟,成為當時四川全境唯壹自給有余的地區。
——川南有三股,分別是王祥、侯永錫和馬應試。
王祥,前明參將,後任遵義總兵。永歷元年(1647年)六月,王祥曾率軍進抵順慶府(今四川南充),命部將王命臣駐守,大肆盤剝百姓。次年,清夔州鎮總兵盧光祖、敘南鎮總兵馬化豹、永寧鎮總兵柏永馥率兵合擊順慶,王命臣潰敗南逃。此後,王祥便盤踞於遵義、江津、合州(今重慶合川)、彭水、黔江壹帶,與貴陽的皮熊遙相呼應。
前明永寧總兵侯永錫的兵力不多,主要在永寧(今四川敘永)壹帶活動。
馬應試原任瀘州衛指揮僉事,此時也拼湊出壹支武裝,盤踞在瀘州、富順壹帶。
——川東南有壹股,即於大海、李占春部。
於大海、李占春是南明重慶守將曾英的義子,曾英被孫可望的大西軍殘部殺死後,於大海、李占春便統率舊部撤離重慶,在涪州(今重慶涪陵)、長壽、墊江壹帶活動。
——川東北有兩股,分別是“三譚”和“搖黃十三家”。
“三譚”是指前明忠州衛(今重慶忠縣)世襲衛官譚文、譚詣、譚弘三兄弟,主要活動在忠州、萬縣(今重慶萬州)、夔州(今重慶奉節)地區。
“搖黃十三家”確切地說不算壹股,而是壹個派系眾多、組織松散的“聯盟”。“搖黃十三家”的前身,是打著“搖黃軍”的旗號,活動在川北地區的農民起義軍。遭到官軍鎮壓後,這些起義軍的殘部紛紛聚攏在川東北的三峽地區。雖然統稱“十三家”,實際上數量遠遠不止十三支。這些勢力類似於占山為王的“山匪”,互不買賬,各自為政,主要首領有袁韜、劉惟明、白蛟龍、呼九思、楊秉胤、景可勤、張顯等人。
四川內戰
四川的局面壹片混亂,既歸因於張獻忠垮臺之後的“半真空狀態”,也跟永歷政權委任四川官員的雜亂無章有直接的關系。
弘光時期,四川作為“寇亂重災區”,官員的任命還是比較有章法的,主要有三位:
“壹號首長”王應熊,字非熊,四川巴縣(今重慶巴南區)人,萬歷四十壹年(1613年)進士。弘光建政後,王應熊被委任為兵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,總督川、湖、雲、貴軍務,專辦“川寇”。孫可望占領遵義時,王應熊躲進山區,於永歷元年(1647年)病逝。
“二號首長”樊壹蘅,字君帶,四川敘州人,萬歷四十七年(1619年)進士。弘光時期被任命為總督川、陜軍務,跟隨王應熊“剿賊”。
“三號首長”馬乾,任四川巡撫,在與入川的清軍作戰中陣亡。
弘光時期的“三巨頭”死了倆,領導班子需要重新組建。永歷朝廷這壹“重組”,徹底亂套了,主要官員的任命如下:
樊壹蘅留任川陜總督。
調偏沅巡撫李乾德任川東北巡撫,不久升任總督。
朱容藩任總督川東軍務。
楊喬然、江而文任巡撫,楊不久升任總督。
詹天顏任川北巡撫。
範文光任川南巡撫。
——糊塗了吧?其實所有人都糊塗!
總督、巡撫這樣的高級官員本該“壹個蘿蔔壹個坑”,結果卻是“壹抓壹大把”,麻煩很快就出現了:聽誰指揮?
名義上歸樊壹蘅統壹指揮,但同為“總督”的李乾德、朱容藩、楊喬然根本不買他的賬,樊壹蘅“無所施節制,但保敘州壹郡而已”,混得比清軍的四川巡撫李國英還要慘。人家雖然也只守著保寧壹府,但好歹說話有人聽,樊壹蘅卻只能“自產自銷”。
李乾德、朱容藩、楊喬然不買樊壹蘅的賬,相互之間也不買賬,下面的巡撫更別提了,全都“各自署置,官多於民”。反正四川軍閥多,靠著壹個是壹個。官帽頂個屁用,全憑槍桿子說話!
各懷鬼胎的朝廷官員,加上擁兵自重的軍閥,整個四川豈止是壹鍋粥,簡直就是壹團亂麻!
福建的亂局,主要表現在“浙系”、“閩系”、“地方系”幾大派系互不買賬、各自為戰,而四川的亂局,除了派系更多、協調更難以外,還有更致命的壹條:抗清的沒有,打內戰大大的有!
從永歷二年(1648年)至永歷三年(1649年),四川內戰頻發,規模比較大的就有四場。
第壹場內戰是楊展、馬應試、王祥之間的“川南會戰”。
王祥盤踞在遵義、江津壹帶,大肆盤剝地方,搞得民不聊生。永歷二年(1648年)初,有人唆使時任四川巡按禦史的錢邦芑,向實力比較雄厚的楊展求援,請他出兵川南“替天行道”、“伸張正義”。
錢邦芑做了多年的禦史,早就養成了嫉惡如仇的“職業病”。聽說王祥在遵義胡作非為,錢邦芑經不住忽悠,果然拍案而起,給楊展寫了壹封求援信。
楊展也是“憤青”壹個,看到錢邦芑的書信,立即決定率師出征,要給王祥壹點顏色看看。
但是,想打王祥並不容易,因為從川西的嘉定到川南的遵義,瀘州是必經之地,而盤踞於此的馬應試不讓道。
好狗不擋道,除非妳欠扁。
楊展不管三七二十壹,對著瀘州的馬應試壹頓狠揍。王祥開始還不知道怎麽回事,正躲在遵義看熱鬧,很快就得知楊展其實是沖著自己來的。——這還了得!妳楊展活得不耐煩了?
王祥果斷率軍出擊,聯合馬應試把楊展給收拾了壹頓。楊展帶來的兵力不多,而且強龍難壓地頭蛇,大敗而歸。
第二場內戰是“川貴之戰”,也是因王祥而起,而且索性打出四川,跟貴州的皮熊幹上了。
遵義距離貴陽不算太遠,中間隔著壹條烏江,王祥壹直都想把實力稍弱的皮熊壹口吃掉。永歷二年(1648年)七月,王祥趁皮熊不備,揮師南下渡過烏江,壹舉包圍貴陽。皮熊被困在貴陽挨揍,貴州將領武邦賢、楊光謙看不下去了,於次月率兵支援,給皮熊解了圍,王祥率部撤回烏江。
皮熊哪裏咽得下這口氣,經短暫準備後,便於十月北上烏江,給王祥來了壹個“以牙還牙”。此後,兩人便在烏江兩岸妳來我往、沖突不斷。由於雙方實力相當,誰也吃不了誰,皮熊、王祥終於在年底決定停火,握手言和。
“川南會戰”和“川貴之戰”都屬於局部性質的軍閥混戰,除了參戰各方有所損失以外,後果還不算太嚴重。接下來的第三場內戰,鬧騰得就比較厲害了,這就是發生在川東地區的“朱容藩之亂”。
朱容藩是楚王朱楨(朱元璋第六子)的遠支後裔,屬於皇親中的“邊緣人物”。張獻忠攻陷武昌的楚王府後,僥幸逃脫的朱容藩開始浪跡天涯,打著“郡王”的旗號四處招搖撞騙。
幾年來,他先後騙過左良玉、馬士英和大順軍,但是都沒有成功,最後總算騙過了丁魁楚,推薦給永歷朝廷,朱由榔安排他執掌宗人府。
宗人府是管皇家事務的,算得上是美差了。可如今兵荒馬亂,皇親死的死、逃的逃,這種差事實在沒有什麽前途。
壹心想出人頭地的朱容藩很快就發現了契機——處於“權力真空”的四川!
朱容藩主動請纓,被朝廷委任為總督川東軍務,取道湘西的辰州抵達湖北施州衛(今湖北恩施),與流落到此的鄖陽守將王光興碰個正著。
來到施州後,朱容藩重操舊業,打起了“楚王世子、天下兵馬副元帥”的旗號,繼續在川東、鄂西地區招搖撞騙。
朱容藩的鬼把戲還真迷惑了壹些人,除了被清軍打得暈頭轉向的王光興以外,於大海、李占春也深信不疑,老老實實地服從朱容藩的號令。
永歷元年(1647年)夏,清軍涪州總兵盧光祖攜搶掠而來的財物、女子,由重慶順江而下,妄圖打通川鄂水道。朱容藩命令於大海、李占春率部果斷攔截,於七月十壹日在忠州大敗盧光祖,清軍殘部退回保寧。
初戰告捷,朱容藩的膽識愈壯。趁著清軍收縮防線,朱容藩帶著受蒙蔽的王光興、李占春、於大海等部,壹面在川東、川南地區“收復”失地,壹面繼續招搖撞騙,忽悠“三譚”、馬應試、楊展,還有“搖黃十三家”中的呼九思、景可勤等歸附自己。
隨著勢力不斷壯大,朱容藩的野心也急劇膨脹。永歷三年(1649年)二月,羽翼漸豐的朱容藩改忠州為“木定府”,堂而皇之地在川東做起了“楚監國”,公然“另立中央”。
朱容藩“自立”,支持的都是被忽悠的,反對的都是不信邪的,而且大有人在。李乾德、袁韜堅決反對,並擊潰了朱容藩派來“清剿”的李占春部。
“憤青”錢邦芑也堅決反對,雖然沒有槍桿子,但他有筆桿子。錢邦芑趕緊向朝廷上疏,又將告狀的疏稿傳閱四川、湘西、鄂西,揭露朱容藩的本來面目。
朱容藩的運氣確實太差,堵胤錫、馬進忠此時正好撤到施州衛休整。得知這個驚天消息,堵胤錫立即派人前往夔州質詢朱容藩:妳說說看,這到底是怎麽回事?
見到堵胤錫的使者,心虛的朱容藩百般狡辯,卻漏洞百出,李占春、於大海、王光興這才恍然大悟,知道自己上了這個“江湖騙子”的當。但是,朱容藩畢竟是皇親,使者也不是朝廷派來的。朝廷沒表態,大家還真拿這個騙子沒辦法。
不過,朱容藩在夔州、忠州是待不下去了。三月,“朱騙子”卷起鋪蓋,移駐萬縣,重金籠絡“搖黃十三家”中的白蛟龍、楊秉胤部作為貼身護衛,又聯絡“三譚”做了靠山,妄圖有朝壹日“東山再起”。
七月,朱容藩手又癢癢了,率部進攻石柱土司。土司向李占春、於大海求援,“受騙者”終於找到收拾“朱騙子”的理由了!
李占春、於大海果斷率部救援,二十五日大敗朱容藩的軍隊,活捉白蛟龍,譚文逃回萬縣,“朱騙子”落荒而逃,最後在雲陽被追兵擒殺。
在永歷朝廷任命的四川官員中,除了“騙子”朱容藩犯上作亂以外,時任川東北巡撫的李乾德也不是什麽好鳥。
“朱容藩之亂”被鎮壓前後,李乾德親自導演了四川的第四場內戰——“川南大火並”。
永歷三年(1649年)初,“搖黃十三家”中的袁韜部“轉戰”到了川南的富順。七月,作為川東北巡撫的李乾德也來到富順。除此之外,原陜西裨將武大定、“搖黃十三家”的呼九思部也先後投奔袁韜。
壹群人聚在富順,雖然身份不同、來路不同,但都有壹個共同點:沒飯吃!(俱絕糧,餓死者甚眾。)
李乾德不愧是朝廷官員,腦子比較靈活,立即給大家出了壹個主意:找四川的“大財主”楊展要!(唯求救於楊展,展若從即無饑乏患矣。)
楊展倒是願意扶貧濟困,但李乾德得寸進尺,又提出了壹個無理要求:讓楊展交出財政大權。
楊展徹底怒了:憑什麽?有本事來搶!
七月二十九日,李乾德與袁韜、武大定合謀(呼九思不久前病死),以袁韜生日為名,擺了壹出“鴻門宴”,將前來赴宴的楊展擒殺,隨即率軍突襲嘉定。
貪戀錢財的李乾德謀害了實力雄厚的楊展,令四川各路軍閥十分寒心。李占春引兵來援,但打不過袁韜,只能悻悻而去。空有總督頭銜的樊壹蘅也看不下去了,寫信斥責李乾德:“背施忘好,而取人杯酒之間,天下其謂我何?”
李乾德不僅置之不理,還將這種卑劣的行徑自詡為“救時大計”,率袁韜、武大定繼續猛攻嘉定,以達到斬草除根的目的。
十二月二十四日,嘉定失守,楊展長子楊璟新率殘部逃往保寧,並於次年正月十六日向清軍投降。
四川痛失最強大的壹股抗清勢力,“自是蜀事大壞矣”。
入川清障
四川亂成這副鳥樣,永歷政權作為名義上的中央,既鞭長莫及,又自顧不暇,只有隨他們瞎折騰。
永歷朝廷全當沒看見,可孫可望看不下去了:妳們精力這麽旺盛,不去抗清也就算了,別擋道啊!
攘外必先安內,抗清必先“清障”,孫可望決定先易後難、殺雞給猴看。
早在永歷三年(1649年)八月,孫可望就派部將白文選率部前往貴州安順,探查皮熊的虛實。永歷四年(1650年)四月,李定國、劉文秀率大軍占領貴陽,以武力逼迫貴州軍閥皮熊、貴州巡撫範鑛“結盟”。皮熊不敢硬頂,只好退守平越(今貴州福泉)伺機而動。
八月,孫可望決定親自趕赴貴陽。平越的皮熊和遵義的王祥都心虛,趕緊給孫可望“表忠心”:咱們都挺聽話的,您老人家就不用親自跑壹趟了。
孫可望哪這麽容易忽悠,根本就不搭理這倆老油條,執意前往貴陽,並派部將馮雙禮、王自奇進攻平越,活捉皮熊。九月,劉文秀、白文選率軍進抵川南的遵義、永寧,逼迫王祥、侯天錫歸附。年底,孫可望的軍隊占領銅仁,整個貴州和川南地區已經納入孫可望的控制範圍。
孫可望的大動作,有效地震懾了只會“窩裏鬥”的四川各路軍閥。在進軍川南、掃蕩貴州的同時,孫可望又與永歷政權在四川名義上的最高長官——川陜總督樊壹蘅取得聯系。樊壹蘅早就想結束亂局,只是苦於無權無兵。
形勢所迫,只談合作。樊壹蘅沒有瞿式耜那麽多“講究”(其實就是階級成見),管妳是大西軍還是大順軍,誰能摁住四川這群刺頭,就跟誰合作!
在樊壹蘅的號召下,大部分四川軍閥“深明大義”,爭先恐後地表示聽從指揮、結束內戰、壹致對外,其實主要是怕被收拾。
在這個世界上,有貪生怕死的,也有豁得出去的。盡管四川的大多數軍閥都歸附了孫可望,但也不乏伸長脖子硬頂的。
李乾德就是壹個脖子硬的。自從導演了“川南大火並”,李乾德帶著袁韜、武大定攫取楊展在嘉定、峨眉地區積累的財富,發了壹筆橫財,也有了跟孫可望對著幹的資本。
樊壹蘅在四川本來就是壹個“光桿司令”,李乾德就是最大的刺頭。暗殺楊展之後,樊總督親自寫信斥責身為川東北巡撫的李乾德,李巡撫曾對樊總督極其鄙視,公然叫囂“救時大計,詎豎儒可知”。樊總督號召各路軍閥“軍令政令統壹”,也就是聽孫可望指揮,李乾德最先跳出來反對。不久後,樊壹蘅病死,李乾德跳得更高,公然以四川最高長官自居。這倒是給壹直想染指四川的孫可望幫了大忙:正愁找不到借口,這回妥了,咱給楊展報仇去!
李乾德級別最高、反對最堅決,所以也最先挨揍。永歷五年(1651年),孫可望作出了分兩路進軍四川的作戰部署,劉文秀率主力渡金沙江,取道建昌(今四川西昌)入川,王自奇部則取道畢節、永寧,奪取川南。
面對孫可望大軍壓境,李乾德決定死扛到底,派武大定率主力前往雅州(今四川雅安)迎戰,另派出壹部兵力駐防敘州。
八月,劉文秀在滎經全殲了武大定的精銳部隊張林秀部,武大定連滾帶爬逃回嘉定,與在嘉定坐鎮的李乾德、袁韜抱頭痛哭壹番之後共同抱頭鼠竄。劉文秀窮追不舍,李乾德、袁韜攜帶的財物太多,走得很慢,終於在仁壽被劉文秀的追兵活捉,武大定落荒而逃。
劉文秀接到的是“斬草除根”的死命令,壹個都不能放跑。如今武大定跑了,但他的兒子武國治跟袁韜在壹起,落到了劉文秀的手裏。劉文秀通過武國治向武大定傳達了“首犯必辦,脅從不問”的寬大政策,已經走投無路又有兒子捏在別人手裏的武大定決定試試運氣,回來“自首”。
事實證明,劉文秀說話是算數的。袁韜、武大定都得到了寬大處理,只有李乾德和弟弟李九德被羈押,送往貴陽治罪。李乾德深知孫可望不會放過自己,與其死得難看,不如自己了斷。押解至犍為境內時,李乾德、李九德趁看守疏忽,投水自盡,好歹留個全屍。
另壹路入川的部隊——王自奇部進展也比較順利,占領永寧後繼續向遵義推進。九月,王自奇將“結盟”以後不怎麽老實的王祥消滅,川南全面平定。
劉文秀做完川西的“善後”,隨即率軍順江東下,聯絡川東武裝,賀珍、王光興、張堯翠等部紛紛與孫可望結盟,宣布“服從領導”。
除了李乾德以外,四川還有壹路軍閥拒絕與孫可望合作——盤踞涪州、長壽地區的李占春、於大海部。
李乾德不合作是因為狂妄自大、貪戀權財,李占春、於大海則另有隱情。孫可望率大西軍余部從西充南下時,在重慶幹掉了南明軍的守將曾英。李占春、於大海正是曾英的“義子”,他們拒絕與“殺父仇人”合作。
在孫可望看來,不管什麽原因,只要抗拒改編,都是欠收拾。劉文秀在收拾李乾德、袁韜的同時,也派出部將盧明臣率軍清剿川東南。李占春、於大海當初想替楊展報仇,結果被李乾德壹頓痛扁。連李乾德、袁韜都揍不過,更別提劉文秀了。
果然,李占春、於大海比李乾德、袁韜死得還要快,七月份就被盧明臣打得四處亂竄。眼看四川已經待不下去了,李占春、於大海向東撤退,準備前往湖北投降清軍。
軍閥想在四川立足很難,但想出川投降也不是壹件容易的事。李占春、於大海的三萬殘軍走到半道上,便遭遇夔東武裝的壹路截殺。夔東地區形勢復雜,山頭眾多,但各路“山大王”如今只有壹個目標:痛打落水狗!
李占春、於大海成了過街老鼠、眾矢之的,壹路損兵折將,跌跌撞撞向湖北靠近,終於在十壹月十壹日抵達清軍的防區。
安全是安全了,但日子不見得好過。清軍荊州總兵鄭四維將前來“投誠”的李占春、於大海部安排在松滋百裏洲休整,接下來的手法跟何騰蛟、瞿式耜如出壹轍:要錢沒有,要糧不給!肚子餓?自己想辦法!
這壹招術相當無恥,卻屢試不爽。當初,田見秀被何騰蛟用這招逼得拍屁股走人,郝搖旗也被瞿式耜逼得四處抓狂。輪到李占春“中招”的時候,麻煩大了。
跑?壹個叛徒,能往哪兒跑?
搶?清軍正愁沒借口收拾妳,莫非嫌命長?
跑不能跑,搶不能搶,李占春終於“看破紅塵”、皈依佛門。——看來,只要逼到沒法活,方法總比問題多!
李占春出家,正中鄭四維的下懷。
其實,鄭四維搞這個把戲的動機,跟何騰蛟、瞿式耜是有本質上的區別的。南明的大臣出於個人利益和階級成見,不惜自毀長城,而鄭四維是想廢掉這支軍閥部隊的武功。
老大出了家,雖然還有個於大海,但基本上已經是群龍無首、人心惶惶,不久便自動瓦解。達到目的後,清軍又招撫李占春“還俗”,先後出任安陸副將、黃州總兵等職,彰顯自己的“博大胸懷”。
劉文秀、王自奇的軍隊在四川大打出手,將李乾德、王祥、李占春幾大軍閥勢力揍得滿地找牙,有效地震懾了其他軍閥。
無論當初表態願意“結盟”的軍閥是出自真心還是假意,如今都死心塌地了。特別是夔東地區的軍閥武裝,親眼見證了李占春、於大海的悲慘境地,紛紛“扼險自守,差人申好”。至此,“三川之阻兵皆盡”,四川(只有保寧仍由清軍控制)、貴州已在孫可望的掌控之中。
抗清的道路通暢了,但孫可望並沒有貿然進軍,因為拿下四川和貴州以後,孫可望的麻煩更大。
——四川和貴州都是吃了上頓沒下頓,好容易有個自給有余的楊展,偏偏又被李乾德給剁了,僅憑雲南壹省之力怎麽養得活?
——大軍出去抗清,後勤補給怎麽保證?有沒有糧食倒是其次,就算有糧食,怎麽穿過四川、貴州送過去?那裏到處都是餓紅了眼的饑民啊!
以前四川、貴州是別人的地盤,孫可望全當看不見。如今兩副爛攤子落到自己的手裏,孫可望終於見識到沒有最爛、只有更爛了。——我說豪格追到遵義怎麽突然放我壹馬,原來這爛攤子簡直是爛得令人發指!
攤子再爛,孫可望也只能埋頭苦修,因為不把四川、貴州的攤子修好,孫可望根本就走不出去。不能走出去發展,三十多萬大軍遲早要被困死在雲南。
貴州涅槃
“流賊”出身的孫可望品行不咋地,既自私又貪權,最後還投降了清軍,但不應該因為這些劣跡而抹殺他在西南的“政績”。
雲南在孫可望的手裏,不出三年便呈現出壹片太平景象。控制四川、貴州之後,孫可望又大力推廣“雲南經驗”。特別是在向來貧瘠的貴州,孫可望確實下了很大的功夫,比較大的措施主要有四個方面:
其壹,統壹軍令政令。
皮熊被活捉後,分散在貴州各地的殘余勢力退守山區、負隅頑抗。除此之外,各地土司也“占山為王”,以前與皮熊抗衡,現在又與孫可望抗衡。凡是外鄉人,他們壹概不鳥。
孫可望派白文選鎮守貴陽後,便開始對南明軍殘余的散兵遊勇、各路山匪進行收編,凡是抗拒收編者壹律清剿,終結了大小軍閥占山為王、殘害百姓的亂局。
其二,裁撤冗員、整頓吏治。
貴州作為南明的屬地,也有官員多如牛毛、官場魚龍混雜的通病,最後的結果都是政府烏煙瘴氣,百姓不堪重負。針對這種狀況,孫可望首先將官員“過篩子”,挨個開展“政審”和清查,欺壓百姓的直接剁掉(戮奸蠹民者),並對南明政權胡亂任命的大量冗員進行裁撤。
篩剩下的官員也別忙著彈冠相慶,因為日子不見得好過。孫可望規定:“凡官員犯法,重則斬首、剝皮,輕者捆打數十,仍令復任管事。”
孫可望不是嚇唬嚇唬,而是動了真格,接下來的這個場景也屢見不鮮:
某官員正端坐堂上審案,對嫌疑犯用刑逼供。此時,突然闖進來壹幫人宣讀“上峰指令”,說某官員犯某某罪,依律杖二十。於是,正趴著受刑的嫌疑犯被拎到壹邊,堂上的官員被拽下來趴上去。打完二十棍,官員、嫌疑犯各歸其位,該審案的審案,該受刑的受刑,就當什麽都沒有發生過。
其三,招徠商賈,安撫百姓,恢復經濟生產。
貴州是喀斯特地貌的山區,找塊跟足球場壹般大的平地基本上不可能,而且石多土少。由於自然環境惡劣,貴州歷來土地貧瘠,交通不便,耕作方式原始(牛都沒法用),再加上軍閥皮熊的大肆盤剝,即便是極其落後封閉的自然經濟也瀕臨崩潰。
在這種情況下,孫可望壹面招徠商賈、恢復貿易,壹面采取“休養生息”的政策,又派軍隊就地組織開荒,“安撫遺黎,大興屯田”,積極恢復農業生產。
其四,發展交通,積極備戰。
李白經劍門關入川,曾留下“蜀道難,難於上青天”的名句。王陽明被流放貴州龍場驛(今貴州修文)時,更有“嘆峰際連天兮,飛鳥不通”的感慨。可以說,“黔道難”比起“蜀道難”,有過之而無不及。
交通,不僅關系到出兵問題,而且直接決定後勤補給能力。“要致富,先修路”是現在的口號,對於孫可望而言,確切的說法是“要打仗,先修路”。
於是,“孫國主”成了“孫總工”,大張旗鼓地開始修路,遇山開道,遇水架橋,貴州的交通狀況得到極大的改善。
道路暢通,既方便了自己,也方便了敵人,孫可望又實行“路印”制度,嚴防清軍間諜趁機混入。
在孫可望的治理下,昔日民不聊生的貴州猶如鳳凰涅槃,初步呈現出壹片欣欣向榮。根據史料記載,貴州“官絕貪汙饋送之弊,民無盜賊攘奪之端”,雖然不免有些誇張,但經濟得到較快的發展卻是不爭的事實。
孫可望治理貴州,主要是為了壯大自己的實力。因此,貴州經濟得到恢復之後,稅賦是相當繁重的。
俗話說“兔子不吃窩邊草”,作為孫可望的老巢,雲南的稅賦是“官壹民九”,達到了全國的最低點。但對於貴州,孫可望可就沒這麽客氣了,稅賦壹般都在五成以上,部分地區甚至達到九成。在孫可望的橫征暴斂下,元氣稍有恢復的貴州再壹次遭受無情的摧殘,為後來清軍順利通過貴州進入雲南清剿,奠定了堅實的“群眾基礎”。
以後的事情以後再說,就目前來看,孫可望還是比較滋潤的。
天無絕人之路
“朱門酒肉臭,路有凍死骨”,當孫可望在西南風生水起的時候,南寧的忠貞營卻在苦苦求生。
自打從湖南敗退入兩廣,沒了堵胤錫的庇護,寄人籬下的忠貞營便開始江河日下。幫陳邦傅打下南寧,陳邦傅不僅不酬謝,還千方百計地想把忠貞營擠走。李錦病死後,高壹功曾率部挺進廣東,幫永歷朝廷抗清,卻屢遭嚴起恒、李元胤、金堡等頑固派的刁難排擠,無功而返。
至永歷四年(1650年)下半年,忠貞營在兩廣已經無法立足,高壹功、李來亨決定轉移。
作決定不難,麻煩的是該往哪裏走。
高壹功、李來亨將地圖壹攤開,發現道路雖然遍布天下,但沒有壹條能讓忠貞營順暢通過。
東面,尚可喜、耿繼茂大軍正在絞殺廣州,永歷朝廷又抵制忠貞營摻和,忠貞營也不想再傻啦吧唧地當炮灰了。
北面,孔有德大軍正在湖南修“爛尾樓”,忠貞營趕過去,正好夠孔有德壹頓午飯。
西面,孫可望的地盤更麻煩,雖然大西軍、大順軍都是農民軍,但張獻忠跟李自成壹直不對付,恩怨由來已久,還曾經為爭奪四川大動幹戈。舊債未了又添新賬,高壹功反對孫可望封王時相當積極。在這種情況下,投奔孫可望,還不如原地待著,受的窩囊氣還少些。
南面,壹片汪洋。
形勢就是這麽壹個形勢,往哪兒走都是送死,忠貞營想討個全屍,似乎只有向南投奔龍王了。
天無絕人之路,只有絕路之人!
思來想去,高壹功、李來亨決定冒壹次險:北出廣西,穿過孔有德、孫可望之間的湘西,進入夔東山區發展。
永歷四年(1650年)十二月,高壹功、李來亨率忠貞營從南寧出發,帶著輜重、家眷,浩浩蕩蕩向北而去。由於擔心受到襲擊,忠貞營不敢走大路,而是選擇崎嶇小道艱難跋涉。
次年,忠貞營按既定路線經過湘西保靖時,遭遇已投降清軍的土司彭國柱襲擊,高壹功中毒箭身亡。臨危受命的李來亨率部突圍,歷盡千辛萬苦,終於率領殘部抵達夔東,與活動在該地區的抗清勢力會合。
抵達目的地後,對永歷政權切齒痛恨的李來亨毅然取消忠貞營的番號,成為夔東山區的“單幹戶”之壹。
隨著忠貞營的“加盟”,過去的“搖黃十三家”逐漸演變成了“夔東十三家”,在川東、鄂西地區利用地理優勢繼續堅持抗清鬥爭。
敬鬼神而遠之
永歷政權將忠貞營逼入絕境,而“逃跑帝”朱由榔自己的日子也不比高壹功、李來亨好過多少。
廣西省會桂林、廣東省會廣州相繼失守,朱由榔逃到南寧避難。但是,清軍此次決心蕩平兩廣,南寧雖然深居廣西內地,也絕非安身之所。
萬不得已之下,朱由榔不得不放下臉面,將最後的希望放到了孫可望的身上。問題在於,朱由榔可以有希望,但孫可望是否接招就得兩說了,畢竟永歷朝廷在“請封之爭”上做得實在太絕。
“逃跑帝”想依靠孫可望“東山再起”(其實就是為了茍延殘喘),“請封”的問題是繞不過去的。由於永歷朝廷已經走投無路,急紅了眼的朱由榔相當果斷:封孫可望為冀王,不爭論!
朱由榔認為自己做了最大的讓步(封“壹字王”),但孫可望依然不改初衷:要麽“秦王”,要麽免談!上次孫可望有所妥協,提出“要敕不要印”的折中方案,這壹次卻坐地起價,敕書、大印壹個都不能少。熱臉貼了冷屁股,朱由榔覺得丟不起這個人,又沒談成。
永歷五年(1651年)二月,孔有德的清軍自柳州南下,揮師直指南寧。逃無可逃的朱由榔急眼了,孫可望比他還要急眼:如果這塊金字招牌沒了,自己這只“潛力股”立馬跌停。
形勢危急,孫可望決定投桃報李,給永歷朝廷送來壹張熱臉——派賀九儀、張明誌率五千精兵協防南寧。
別看孔有德人多勢眾,還真不壹定幹得過裝備精良、訓練有素、以逸待勞的五千精兵,孫可望對此胸有成竹。
孫可望不是活雷鋒,五千精兵也不是“保護”永歷朝廷的“誌願者”。賀九儀、張明誌進入南寧後,主要幹了三件事:
其壹,布置南寧城防,抵禦可能進犯的清軍。
其二,對“請封之爭”中的“頑固勢力”反攻倒算,殺死兵部尚書楊鼎和,逼死大學士嚴起恒,向朱由榔示威。
其三,為孫可望請封“秦王”。
撞破南墻始回頭,見到棺材方落淚,朱由榔終於屈服了。如今,南寧在別人的手裏,兩只“死雞”擺在自己面前,朱由榔實在找不到拒絕的底氣。
三月,永歷朝廷正式冊封孫可望為“秦王”,歷時兩年的“請封之爭”總算是塵埃落定。
孫可望如願以償,但並沒有給朱由榔好臉色。對於孫可望而言,永歷朝廷和朱由榔,不過是招搖過市的幌子、壯大實力的招牌。貼壹張熱臉,孫可望不是為了給自己找個大爺。朱由榔倒是好對付,只會在朝堂上唧唧喳喳的大臣才是大麻煩。
因此,孫可望對待永歷朝廷和朱由榔,始終奉行壹條基本原則:“敬鬼神而遠之。”——控制朝廷是必須的,但廷臣想唧唧歪歪,免談!
既想“敬”又要“遠”,思維很獨到,但問題是不太現實。馬士英、鄭芝龍想做到,但都沒能做到,他們把持朝政的同時,也飽受群臣的攻訐。這個看似無解的“夢想”,到了孫可望這裏,神話成了現實。
孫可望得到“秦王”的冊封,宣布效忠朱由榔,接著只做了壹件事:在貴陽建立行營六部(相當於“臨時中央”),以自己的親信充任各部尚書。
朱由榔帶著為數不多的大臣留在南寧,孫可望並沒有讓他們搬家的意思。於是,貴陽的“臨時中央”實際上取代了南寧的“正式中央”,朱由榔還是朱由榔,不過不再是權臣手中的“傀儡”,而是神龕上的“牌位”。
孫可望為了權力不擇手段,但楊畏知是個厚道人。奉命前往南寧時,楊畏知實在看不慣賀九儀、張明誌在這裏狗仗人勢,奮筆上疏彈劾。
看到楊畏知的奏疏,朱由榔眼淚嘩嘩的:千金易得,知己難尋,終於有人肯說句公道話了!朱由榔雖然不敢拿賀九儀、張明誌怎麽樣,但提拔楊畏知入閣還是可以的。
很多時候,講公道、說真話是要付出代價的。
在朱由榔看來,褒獎楊畏知,是在跟孫可望套近乎。但對權力極其敏感的孫可望不這麽看,他認定楊畏知背叛了自己。是在“賣主求榮”。
永歷五年(1651年)五月,楊畏知被孫可望派人押回貴陽處死。——這就是楊畏知說句公道話的代價,但孫可望未必是真正的贏家。既然永歷政權威信掃地,孫可望又能身價幾何?出來混遲早要還,孫可望當然也會付出代價,只是需要壹點時間而已。
此時的孫可望小人得誌、趾高氣昂,“逃跑帝”朱由榔卻是如履薄冰、膽戰心驚。十壹月,朱由榔最不想看到的壹幕終於發生了——孔有德大軍逼近南寧。
賀九儀、張明誌的五千精兵是否願意防守南寧、是否有能力守住,應該都不是問題,畢竟孫可望並不希望這塊“金字招牌”落入清軍之手。問題在於,朱由榔根本就不是固守的性格。
老大坐鎮指揮、鼓舞士氣,將來犯的清軍打得抱頭鼠竄。——朱聿鍵會這樣做,但對於靠逃跑過日子的朱由榔而言,無異於“逆天”!
打不贏要跑,打得贏也要跑,這才對得起“逃跑帝”的名望。可是,這壹回咱們往哪兒跑?
就當前的形勢來看,朱由榔有三個選擇:
其壹,向海上逃亡,投靠福建沿海的鄭成功部。
不靠譜!
鄭成功雖然口頭上奉永歷為正朔,但大難臨頭是否會接收這位爺?——不壹定!
即便鄭成功肯“收容”,他會不會步鄭芝龍、孫可望的後塵?——很有可能!
做傀儡倒還在其次,可鄭成功自己都饑寒交迫、漂泊不定,朱由榔能跟著混多久?
總之,風險太大!
其二,向南逃往越南避難。
更不靠譜!
越南是明朝的屬國,什麽是屬國?有奶便認娘,強悍便認爹!妳信不信,只要朱由榔邁出國門,越南王立即就能將他五花大綁,“遣返”給孔有德,做歸附清朝的“投名狀”。
其三,向西進入孫可望的地盤。
相對而言,這個選擇稍微靠譜壹點,孫可望也早在五月就提出移蹕雲南的動議,但朱由榔壹萬個不願意。孫可望是什麽人,他不是沒見識過。寄人籬下的生活,用腳趾頭都能想到該會有多丟人、多悲慘。
朱由榔“不欲就可望”,但很多事情不是他說了算的。朝議之中,三種選擇都有人提了,接著輪到首輔吳貞毓拍板。其實,這板根本沒必要拍。地球人都知道,永歷朝廷除了歸附孫可望,已經別無選擇。但是,吳首輔曾經跟隨嚴起恒極力反對孫可望封王,嚴起恒、楊鼎和屍骨未寒,擔心“拉清單”的吳首輔實在不敢拍這個板。
“搬家”問題久拖不決,賀九儀怒了:不去拉倒,妳們愛上哪兒上哪兒,我不管了!
賀九儀帶著五千精兵跟永歷朝廷“拜拜”,朱由榔急了:還討論個屁,跑啊!
往哪兒跑?——還能往哪兒跑?有選擇余地嗎?
十二月初,朱由榔乘船倉皇逃離南寧,溯左江至瀨湍(今廣西崇左附近)。上遊水太淺,船沒法再繼續走,朱由榔壹行人棄舟登岸,經龍英(今廣西大新附近)、歸順(今廣西靖西)、鎮安(今廣西德保),向雲南進發。
清軍窮追不舍,跑得賊快的朱由榔第壹次逃跑得如此膽戰心驚,所幸在桂、滇邊境與前來“迎駕”的狄三品、高文貴、黑邦俊部撞個正著。雖然驚魂未定,但此次提心吊膽的歷程總算終結了。
永歷六年(1652年)正月初壹,朱由榔在雲南邊境的壹個小山村裏過了壹個慘兮兮的新年。朱由榔不知道,接下來該去哪裏,確切地說,將會被孫可望安排到哪裏去。
強顏歡笑過完年,朱由榔在“迎駕”部隊的帶領下,繼續艱難跋涉,半個月後抵達廣南府。憑心而論,朱由榔並不想去昆明或者貴陽,天天看著孫可望的臉色過日子。他想就此留在廣南,舒舒坦坦了此殘生。
朱由榔的想法,孫可望壹般都不會支持,他不希望永歷朝廷賴在廣南不走。既然是“敬鬼神而遠之”,廣南府似乎還不算遠。當然,這話不能明說,冠冕堂皇的理由是:廣南靠近邊境,不可預知的風險較大。(廣南雖雲內地,界鄰交趾,尚恐敵情叵測。)
廣南不能住,昆明、貴陽更別提了,朱由榔不想去,孫可望更不讓去。那麽,永歷朝廷往哪裏擺?孫可望物色了壹個相當遙遠的“風水寶地”——貴州安隆千戶所,朱由榔駐蹕後改為安龍府。
遙遠,有時候不單指空間上的距離。安龍的遙遠,超乎所有人的想象。
安龍位於貴州、雲南、廣西三省交界處,原是隸屬貴州都指揮司的“千戶所”,屬於屯兵機構。這座位於大山深處、居民只有百余戶的所城,地域相當狹小,十分鐘便能繞著城走壹圈。(所城圍壹裏二百七十步。)
從南寧到廣南,再到落腳安龍,朱由榔只有壹個感覺:距離“九五之尊”越來越遠。這哪裏是移蹕,簡直就是落草!
永歷朝廷自己沒本事,將地盤丟個精光,淪落到寄人籬下的地步,確實也沒底氣講什麽條件,只有“客隨主便”。二月初六,朱由榔帶著五十余文武大臣、三千兵丁家眷,步履蹣跚抵達安龍。
壹無所有的朱由榔,真正過上了“孤家寡人”的悲慘生活。(王自入黔,無尺土壹民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