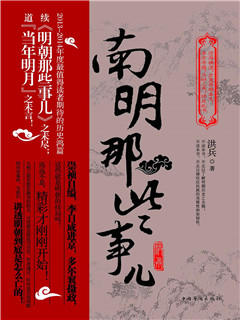- [ 免費 ] 第壹章 詭異
- [ 免費 ] 第二章 抉擇
- [ 免費 ] 第三章 國策
- [ 免費 ] 第四章 疑案
- [ 免費 ] 第五章 湮滅
- [ 免費 ] 第六章 抗爭
- [ 免費 ] 第七章 雄起
- [ 免費 ] 第八章 困境
- [ 免費 ] 第九章 殘夢
- [ 免費 ] 第十章 內訌
- [ 免費 ] 第十壹章 驚變
- [ 免費 ] 第十二章 敵後
- [ 免費 ] 第十三章 中興
- [ 免費 ] 第十四章 危局
- [ 免費 ] 第十五章 南下
- [ 免費 ] 第十六章 後方
- [ 免費 ] 第十七章 整頓
- [ 免費 ] 第十八章 反攻
- [ 免費 ] 第十九章 合流
- [ 免費 ] 第二十章 密謀
- [ 免費 ] 第二十壹章 敗局
- [ 免費 ] 第二十二章 滄海
- [ 免費 ] 第二十三章 殉難
杏書首頁 我的書架 A-AA+ 去發書評 收藏 書簽 手機
简
第十八章 反攻
2018-9-27 20:44
狹路相逢勇者勝
孫可望比較強悍地整頓四川、貴州,比較無恥地收拾永歷朝廷,最初的動機其實比較單純,那就是執行張獻忠“爾急歸明,毋為不義”的臨終托付,壹門心思抗清。
抗清,必須有統壹的領導,不服氣的要摁住(李定國、劉文秀)、不聽話的要收拾(四川、貴州軍閥)、沒本事的靠邊站(永歷君臣),這就是孫可望的邏輯。
南明這麽多年的歷史證明,清軍很多時候喜歡“不請自到”。當孫可望壹面經營西南、壹面為“請封”跟永歷朝廷慪氣時,北京方面有了新動向。
永歷六年(1652年)二月,吳三桂、李國翰奉順治皇帝的命令(多爾袞在前壹年底病死),率軍自漢中入川,進抵保寧。
吳三桂率幾萬大軍奉命前來,顯然不是幫著李國英守保寧,而是意圖進取四川的。由於孫可望正在貴州集結兵力準備入湘,留在四川的留守部隊並不多,因此吳三桂的進攻速度相當快。
吳三桂率軍自保寧南下,先清剿川西的孫可望勢力。二十二日,清軍進抵成都,守將林時泰兵力單薄,不戰而降,被清軍處死。二十五日,嘉定失守。
三月,清軍向川東方向運動,初五占領合州。鎮守重慶的盧明臣也沒多少人,於十四日棄守重慶,主動後撤。四月,川南的敘州告急,守將白文選也選擇了主動後撤,退往永寧。隨後,清軍在四川攻城略地,將孫可望的勢力剿滅或者驅逐殆盡。
孫可望想到清軍會來,但沒有想到來得如此迅速,趕緊派劉文秀部署入川抗清。
狹路相逢勇者勝!與不可壹世的清軍壹決雌雄的時刻終於到了!
孫可望、李定國、劉文秀、艾能奇,張獻忠手下的這四員猛將,個頂個的打架天才,都不是吃素的貨。
“老大”孫可望的本事,我們已經見識過了,西南三省不是吹出來的,是實實在在打出來的!艾能奇轉戰千裏、戰功顯赫,最後在雲南“剿匪”時,陰溝裏翻了船。
現在,終於輪到劉文秀上場了!
大腕出場,不同凡響,劉文秀率部入川果然是大手筆。劉文秀帶著四萬多人,不是選擇壹個方向入川,而是兵分三路,從川西南的建昌、川南的永寧、川東南的彭水同時推進。
敢這樣入川打架的,迄今為止獨此壹人!
劉文秀的靈魂深處,有壹股不服輸的勇氣,更有壹股舍我其誰的傲氣!
八月初九,中路軍率先告捷,全殲鎮守敘州的清軍,並會合白文選部反攻重慶。同時,西路、東路也秋風掃落葉,快速向北推進。
吳三桂嚇傻了:雖說出來混遲早要還,這還得也太快了吧?
八月十九日,清軍在四川的“三巨頭”——吳三桂、李國翰、李國英在夾江開了壹次重要會議,會議做出了壹個極其重要的決定——撤!
大家都是聰明人,都明白“打得贏就打,打不贏就跑”的道理。“撤退”的共識很快達成,但分歧在於:撤到哪裏去?
三個人,兩種意見:A.四川保寧;B.陜西漢中。
李國英選A。——幾萬大軍壹拔腿就撤到陜西,我這個四川巡撫怎麽向朝廷交代?
吳三桂、李國翰選B。——多說無益,安全第壹。妳怎麽交代是妳的事,妳的事關我們屁事?
二比壹,少數服從多數,開溜!
“夾江會議”的決定很快傳達到分散在四川各地的清軍,大家接到命令便拔腿開溜,向陜西方向撤退。
各路清軍跑得不亦樂乎,只有重慶的清軍比較悲催。
當時,駐紮在重慶的清軍將領有壹大幫子,包括梅勒章京葛朝忠、白含真、佟師聖、鑲紅旗章京尹得才、永寧總兵柏永馥、左路總兵陳德、夔州總兵盧光祖等等。接到吳三桂的命令後,諸將領趕緊率各部後撤。
八月二十五日,劉文秀會合白文選的部隊進抵重慶,突然發現很不對勁:清軍死哪兒去了?
雖然各地軍隊都發現清軍在後撤,但重慶的清軍“不翼而飛”,讓劉文秀有點如鯁在喉的感覺,這跟他入川的重大使命有很大關系。
什麽重大使命?不是抗請嗎?——對,但不全對!除了清剿吳三桂、李國翰、李國英以外,劉文秀還肩負壹項重任:打通川鄂通道,為將來順江東下掃清障礙。
這條抗清的道路,富有遠見的孫可望已經盤算很久了。就目前的形勢來看,如果單純采用“推土機”戰術,從貴州經湖南、江西、浙江,壹路推到南京,難度顯然是相當大的。但要是控制了長江這條“黃金水道”,進軍南京的難度至少可以打個對折。
顯然,重慶的守軍“人間蒸發”,對於長江水道的暢通,隱患是相當大的。因此,劉文秀不敢怠慢,趕緊率軍日夜兼程向北追擊。
二十八日,在距離重慶壹百多裏的停溪,劉文秀的追兵終於看到了清軍的影子,隨即像餓綠了眼的惡狼見到肥肥的綿羊壹般撲了上去。葛朝忠等人哪裏想到會臨時加上這出戲,登時驚慌失措、亂作壹團,成了劉文秀大軍的活靶子。
最後,壹大群將領中只有永寧總兵柏永馥僥幸得以保全,帶著幾百殘兵敗卒,踉踉蹌蹌逃至保寧。
劉文秀帶著幾萬大軍在四川各地窮追猛打,招架不住的清軍紛紛後撤,四川的局面基本上又回到了戰前狀態。
“衰神”之保寧之戰
九月十壹日,吳三桂、李國翰、李國英撤到綿州(今四川綿陽),接著又撤往川、陜邊境的廣元。眼看就要進入陜西境內,李國英屢次反對無效,但保寧終於有人看不下去了。
看不下去的人,是時任四川巡按禦史的郝浴。當時,郝浴帶著總兵嚴自明鎮守保寧。雖然有個總兵在身邊,但這個總兵充其量算個連長,手下就壹百來號人,實在是悲慘到了極致。
吳三桂、李國翰二話不說準備撤回陜西,郝浴便頻繁派人給吳三桂帶話,好言相勸之余也不乏恫嚇威脅:奉旨入川,卻棄守四川,這可是欺君之罪!奉勸妳出川之前,先摸壹摸自己有幾個腦袋,免得徒增“早知今日,何必當初”的哀嘆,毀壹世英名於壹旦!
李國英反對,吳三桂可以充耳不聞,但郝浴出聲,吳三桂必須掂量掂量,他知道這個“奉旨告禦狀”的禦史不好惹。
從吳三桂入川起,郝浴的彈劾奏疏就沒有斷過,今天告他“驕恣部下、淫殺不法”,明天告他“殘暴無紀律”。雖然朝廷沒有把手握重兵的吳三桂怎麽樣,但確實讓吳三桂不厭其煩。
“好鞋不踩臭狗屎”,吳三桂經過壹番深思熟慮,還是改變了決定,率領後撤大軍於九月十九日折返保寧。
此後,郝浴算是跟吳三桂扛上了,屢次上疏彈劾。吳三桂屁股也不幹凈,每次都被點到要害。被踩了尾巴的吳三桂絕地反擊,兩人吵得烏煙瘴氣。“欺軟怕硬”的順治皇帝不想攬這筆爛賬,索性將郝浴流放到關外了事。直至吳三桂造反,郝浴才得到赦免,重返官場。
劉文秀率軍入川,用了不到兩個月,便將清軍打回原形,保寧恐怕也難以保全。但是,隨著吳三桂、李國翰、李國英返回保寧,川北的形勢發生了變化。更要命的問題是,壹路凱歌高奏的劉文秀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。
驕兵必敗,這是壹個極其危險的信號,劉文秀很快就會變成“衰神”!
在劉文秀看來,收復全川只剩下最後壹步。不動則已,動則不留遺憾,劉文秀決定畢其功於壹役。
十月初二,劉文秀率大軍進抵保寧,將固守的清軍團團圍困。
客觀地說,劉文秀乘勝進攻保寧,算不上戰略失誤,畢竟自己掌握著整個四川戰場的主動權。但是,靈魂深處的傲氣、輕而易舉的勝利,讓劉文秀失去了必要的理智與穩重。
他忽略了壹個至關重要的現象:大軍壹路攻城略地,收復了保寧以外的四川全境,但消滅的清軍並不多!
除了重慶以外,四川各地的清軍大部分都不戰而逃、“人間蒸發”。這些人去了哪裏?顯然,答案有且只有壹個——保寧!
各地清軍退守保寧,再加上吳三桂、李國翰親率的部隊入城,保寧清軍的實力已經不可小覷。在兵力不占絕對優勢的情況下,劉文秀不經細致準備,便貿然組織對保寧的進攻,戰略上是相當失策的。
戰略上的重大失誤,或許是因為劉文秀情報不明,又掉以輕心,似乎還情有可原。但是,劉文秀急於剿滅清軍的有生力量,在戰術上犯了壹個相當沒有技術含量的低級錯誤——“鐵桶戰術”。
大軍進抵保寧後,劉文秀將保寧包圍得水泄不通,並從各個方向向城內固守的清軍發起全面攻擊。
這個戰術似乎沒有什麽問題,當年堵胤錫率領忠貞營圍攻長沙,也是這麽幹的。要不是何騰蛟瞎攪和,拿下長沙也就是壹兩天的事情。這麽強悍的戰術,到了劉文秀這裏,怎麽就成了低級錯誤呢?
打仗是門技術活,具體問題得具體分析,生搬硬套是要不得的!
——“鐵桶戰術”的前提是對敵形成壓倒性優勢,但隨著保寧的清軍得到大量補充,劉文秀的這種優勢蕩然無存。
——保寧跟贛江壹樣,也是三面環水,不過是由嘉陵江彎成“U字形”形成的,東、西、南三面被江水阻隔,易守難攻。
在這種情況下采取“鐵桶戰術”,對於壹個身經百戰的將領而言,確實是不可原諒的。
戰略失誤,戰術繼續失誤,“衰神”劉文秀的敗局不可避免。
十月十壹日,劉文秀率五萬軍隊從四面攻城,主攻是沒有河流阻隔的北面,並將嘉陵江上的浮橋全部砍斷,企圖將吳三桂、李國翰困死在保寧。
插翅難逃的吳三桂絕地反擊,對準劉文秀大軍中最薄弱的張先璧部發起猛攻。張先璧潰敗,沖散了毗鄰的王復臣部,劉文秀大軍陷入壹片混亂之中。吳三桂、李國翰趁機采取“亂棍戰術”,更是亂上加亂。
由於三面河流上的浮橋被砍斷,劉文秀大軍陷入了絕地,遭遇慘敗,王復臣、姚之貞等將領陣亡,劉文秀率余部撤回貴州境內。孫可望念其勞苦功高,只是解除兵權,送回昆明賦閑;對後來歸附的張先璧就不必客氣了,直接命人拖出去亂棍打死。
躊躇滿誌的劉文秀敗得壹塌糊塗,四川又落到了清軍的手裏;勉強留守的吳三桂勝得稀裏糊塗,也不敢貿然擴大戰果。自此,四川轉入僵持狀態,孫可望打通川鄂水道的設想落空,成為壹大憾事!
“戰神”之靖州大捷
四川意外失手,但湖南卻有意外的驚喜。
入湘抗清,孫可望已經盤算好幾年了。早在永歷五年(1651年)四月,孫可望便派部將馮雙禮作為“開路先鋒”,率四萬多人(包括騎兵壹萬多,還有戰象十余頭)進入湖南境內。
有意思的是,清軍“三王”南下兩廣,七拼八湊才攢足四萬人。孫可望打湖南壹個省,光是“開路先鋒”就不止四萬,還有大象助陣,這排場可真夠大的!
跟南明政權交鋒的幾年來,清軍似乎只有受降的時候才見過這麽多人!
馮雙禮率領的這支“先鋒部隊”從貴州出發,於四月十五日進抵湖南沅州。清軍在沅州的守軍有多少呢?
三千人!
沅州之戰,就是壹場“要妳命三千”的殺人遊戲。毫無懸念,搞“鐵桶戰術”的馮雙禮初戰告捷,清軍守將鄭壹統、知州柴宮桂被俘獲。
馮雙禮的第二站是沅州北面的辰州,駐守在此的是清軍辰常總兵徐勇。徐勇是個相當抗打的貨,帶著幾千人精心布置防線,扼險固守、負隅頑抗,人生地不熟的馮雙禮沒能打下來。
老馮沒有劉文秀的傲氣,能夠比較坦然地接受現實。既然奉命打整個湖南,有足夠的空間發揮和表現,沒必要計較壹座孤城的得失。
辰州的徐勇松了壹口氣,輪到駐守寶慶的沈永忠抑郁了。
為了解除孔有德南下的後顧之憂,他被清廷從山東調到湖南修“爛尾樓”。壹年多來,沈永忠帶著兩萬人轉戰湖南各地,跟各式各樣的“釘子戶”鬥智鬥勇。如今“釘子”沒拔完,又闖進四萬人來搶飯碗,沈永忠實在是欲哭無淚。
憑借做了壹年多“東道主”的“主場”優勢,沈永忠帶著兩萬人與馮雙禮的四萬大軍艱難周旋。雙方妳來我往,各有勝負,湖南很快便進入僵持狀態。
吳三桂、李國翰奉命率軍到四川撒野,並沒有改變孫可望進軍湖南的既定計劃。
馮雙禮的四萬人不過是“開路先鋒”,那麽進取湖南的主力是誰呢?前面說過,在整個南明時代,能把清廷打急眼的只有兩個人,壹個是在陜西點火燒後院的姜瓖,另外壹個,便是堪稱南明“戰神”的原大西軍安西將軍——李定國。
有點可惜,輪到“戰神”出場的時候,多爾袞已經死翹翹了,急眼的人變成了親政不久的順治皇帝福臨。
永歷六年(1652年)四月,“戰神”李定國率十萬大軍進入湖南,戰場的力量對比發生逆轉。
五月中旬,李定國會合馮雙禮部進攻靖州。沈永忠此時還不知道李定國大軍已經入湘,誤以為又是馮雙禮在找茬,便派麾下總兵張國柱率八千兵馬前往靖州支援。
幾天之後,李定國大軍取得“靖州大捷”,遍體鱗傷的張國柱逃回寶慶。沈永忠清點了壹下人數,還剩下兩千多人,立馬傻眼了:妳是打架去了,還是集體自殺去了?
張國柱對作戰經過做了壹番描述,沈永忠聽得毛骨悚然。他敏銳地感覺到,這次在靖州鬧騰的並不只是馮雙禮的部隊。
看來,孫可望開始對湖南下狠手了!
沈永忠只猜到孫可望非拿下湖南不可,卻怎麽也沒想到,自己的對手會是南明最強悍的“戰神”李定國。
湖南危急,沈永忠能想到的最佳辦法,就是趕緊派人到桂林,懇請孔有德回師救援。
救,還是不救?
孔有德不需要權衡商議,更不需要扔硬幣,在第壹時間便給出答復:沒空!
孔有德如此絕情,打醬油的都看不下去了。要不是幫妳把守後院,老沈也不會大老遠被調過來接這個爛攤子。如今老沈落難,妳老孔竟然見死不救,未免太不仗義了吧?
圍觀群眾往往都是不明真相的,其實孔有德有足夠的理由拒絕:
其壹,報沈永忠的“壹疏之仇”。
進軍廣西後,由於後勤補給壹時跟不上,孔有德曾經向衡州、永州借支糧餉,並承諾有借有還。屁大點事,沈永忠卻壹封奏疏捅到朝廷上去,搞得孔有德十分難堪。
其二,沈永忠謊報軍情。
孔有德判斷,廣西有自己的大軍坐鎮,孫可望不可能派大部隊進入湖南,除非他的雲南、貴州不想要了。因此,壹定是沈永忠自己沒本事,打了敗仗就怪對手太強悍。
其三,兵力難以在短時間內收攏。
孔有德雖然坐鎮省會桂林,但三鎮總兵分別鎮守在廣西各地,線國安駐南寧、馬雄駐梧州壹帶、全節駐柳州(原配屬的曹得先、馬蛟麟兩位總兵已調離),收攏起來相當麻煩。
其四,大軍北撤,廣西怎麽辦?
根據以往的經驗,清軍撤離之後,各種抗清勢力比雨後春筍冒得還要快。兩萬大軍回援湖南,能否幹掉李定國、馮雙禮還很難說,就算幹掉了,妳沈永忠還能重新把廣西拿下來嗎?
說壹千道壹萬,各端各的碗、各吃各的飯。李定國在湖南,歸妳沈永忠管。他敢打到廣西,我負責收拾,不用妳沈永忠摻和。(設警逼我境,自有區處。)
救兵搬不來,打又打不過,所幸沈永忠還剩下壹條路——跑!
從寶慶北撤這壹路,沈永忠是食不甘味、夜不能寐。在他看來,至少有兩個人會要他的命:壹是李定國,壹是順治帝。
李定國的追兵容易躲,大不了多走幾天山路而已。如果順治帝要追究“失地之罪”,沈永忠擺什麽姿勢都要中槍。
沈永忠膽戰心驚地走到湘潭,接到了順治帝下達的密旨——“不可浪戰,移師保守”,壹切都妥了!
奉旨撤退,再沒有比這更愜意的事情了!
有了這道“護身符”,沈永忠跑得飛快,也撤得相當徹底。六月初二進入長沙後,索性壹不做二不休,於八月初六主動棄守省會,退往嶽州。
沈永忠跑了,湖南各地的官員、武裝也紛紛“樹倒猢猻散”,開展“逃跑大比拼”。很快,除了嶽州、常德、辰州以外,李定國已收復湖南絕大部分地域。
“戰神”之桂林大捷
四川打得只剩下壹個保寧時,“衰神”劉文秀沈不住氣,結果骨頭沒啃下來,倒把門牙崩壞了兩顆,被孫可望打發回昆明“休假式療養”去了。此時的湖南還剩下三座城池,李定國卻決定“見好就收”。——是否具有敢於舍棄的遠見與胸懷,往往決定著能力水平的高低!
湖南可以先放壹放,李定國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辦——收拾孔有德!
此時,孔有德還在做著他的“春秋大夢”,認為湖南的局面不足為慮。盡管湖南各地相繼被李定國的軍隊收復,孔有德除了在五月底派壹部兵力駐守全州“警戒”以外,再未作更多的防備。
六月二十八日,李定國率大軍自武岡、新寧進攻全州,原駐防軍加上派來“警戒”的清軍被“壹鍋端”。戰報傳來,孔有德大為震恐,次日親率桂林的留守部隊趕赴嚴關防禦。
李定國乘勝進抵嚴關,將清軍揍得七葷八素,孔有德當天便倉皇撤回桂林固守。六月三十日,李定國的前鋒部隊進抵桂林郊外。七月初二,桂林陷入重圍,孔有德趕緊派人通知線國安、馬雄、全節,令三鎮總兵火速回援桂林。
桂林危在旦夕,三鎮總兵又不是空軍。回援之路要壹步壹步地走,而壹切都已經太晚了!
七月初四,李定國率軍攻破桂林,悔恨交加的孔有德選擇了自盡,史稱“桂林大捷”。茍且偷生於桂林城內的陳邦傅、王荃可、張星光等降清大臣被活捉,並於九月在貴陽伏誅。其中,惡貫滿盈的操蛋分子陳邦傅受刑待遇最高——剝皮揎草,傳示滇黔!
幹掉孔有德不是唯壹目標,奪取桂林更不是終點,“戰神”李定國繼續率軍南下。孔有德自行了斷後,輪到線國安、馬雄、全節傻眼了:主將都嗚呼哀哉了,還打個鳥仗?
三鎮總兵壹溜煙撤到梧州,李定國在廣西收復失地,忙得不亦樂乎。八月,終於騰出手來的李定國向梧州推進,線國安、馬雄、全節不戰自潰,逃往廣東投奔了尚可喜。
八月十五日,李定國占領梧州,廣西至此全部光復。四個月的時間,“戰神”壹舉拿下兩個省!
尚可喜曾經遭到孔有德的恥笑,如今孔有德死這麽慘,尚可喜實在是沒有幸災樂禍的雅興。不是老尚胸懷寬廣不記仇,而是李定國的大軍太強悍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話,自己很快就會成為下壹個孔有德。
令人大跌眼鏡的是,尚可喜臆想的“意外”,偏偏意外地發生了。
李定國的大軍已經在廣西邊境的梧州集結,準備揮師向東收拾尚可喜,卻接到了孫可望的命令——火速回援湖南!
回援湖南?那裏出了什麽狀況?莫非沈永忠“原地滿血復活”還“裝備升級”?
怎麽可能!沈永忠壹直都是半死不活。真實的情況是:湖南來了“新客”——清敬謹莊親王尼堪。當然,尼堪不是單刀赴會,而是帶著幾千八旗精兵來的。他也不是來觀光的,而是來找人打架的。直白地說,是來給沈永忠“報仇”兼“撐腰”的。
原來,順治皇帝見湖南打得太不像樣,擔心影響兩廣的態勢,於七月十八日委任尼堪為定遠大將軍,率八旗兵南下。
按照原定計劃,尼堪率軍經湖南進入貴州,會同四川的吳三桂、李國翰搗孫可望的老巢,演壹出“螳螂捕蟬,黃雀在後”的好戲,順帶把朱由榔請到北京“把酒言歡”。
但是,尼堪走到半道上,孔有德“殉難”的噩耗便傳到了北京。順治帝趕緊在八月初五重新下達命令,讓尼堪拿下湖南後向廣西推進。
同時,順治帝又給廣東的尚可喜、耿繼茂下了壹道死命令:固守待援,保存實力,不準去廣西犯賤!(切毋憤恨,輕赴廣西;倘賊犯廣東,爾等宜圖萬全為上計。)其實,順治帝未免多慮了。尚可喜天天提心吊膽,捏雙筷子手都發抖,哪裏還敢去廣西送死。
尚可喜沒敢動,但尼堪的八旗兵距離湖南越來越近。湖南壹旦有失,貴州恐怕危矣,所以孫可望急眼了,趕緊命進軍廣西的李定國回撤。
客觀地說,家大業大的孫可望逐漸變得跟劉文秀壹個毛病——不穩重、不淡定,缺乏“泰山崩於前而面不改色”的氣魄,更缺乏“會當淩絕頂,壹覽眾山小”的戰略眼光。
基於當時的態勢來分析,孫可望的決定相當草率、相當幼稚。
其壹,李定國率大軍滯留兩廣,對清廷是壹個重要的威懾。他們擔心,兩廣壹旦有失,必然導致西南的朱由榔、孫可望與東南的鄭成功、魯監國連成壹片。因此,尼堪未必敢大舉進攻貴州,西南老巢還是安全的。
其二,尼堪大軍進入湖南尚需時日,在湖南打開局面也需要壹定的時間。李定國即使要回援,也有足夠的時間先進軍廣東,將尚可喜、耿繼茂揍得“生活不能自理”,再從容地經韶州、郴州北上迎戰尼堪。
其三,即使李定國從廣西回援,也不應全軍北上,廣西至少需要留下足以抗衡尚可喜、耿繼茂挑釁的留守部隊。李定國手握十萬大軍,留下壹半兵力守在梧州、桂林,尚可喜、耿繼茂根本不敢動,而五萬大軍收拾尼堪,顯然是綽綽有余。
遺憾的是,所有不該犯的錯誤,孫可望、李定國全犯了。十月三十日,李定國率十萬大軍回撤至衡州。
李定國大軍撤退後,新任的廣西巡撫徐天佑帶著壹兩千人鎮守梧州,安西將軍朱喜三則率領壹千多烏合之眾駐防桂林,其余各地的防守兵力更加單薄,廣西頓時空空如也。
來勢洶洶的李定國大軍突然沒了蹤跡,僥幸脫險的尚可喜膽識愈壯。為了探查廣西的虛實,李定國前腳剛走,尚可喜就令孔有德麾下的三鎮總兵線國安、馬雄、全節率部返回廣西。(順治帝曾下令尚可喜、耿繼茂不準去廣西犯賤,所以尚軍自己不敢亂動。)
九月初五,三鎮總兵占領梧州,寡不敵眾的徐天佑只得後撤桂林,又於十壹月底撤至柳州。廣西兵力如此空虛,線國安等人竟然磨蹭到十二月下旬才占領平樂。從梧州打到平樂區區四百裏,花了將近四個月,三鎮的戰鬥力也實在是爛得可以。壹直到次年正月,清軍才相繼攻取陽朔、桂林,勉勉強強“收復”了廣西。
“戰神”之衡州大捷
交待完廣西,再來說湖南,“戰神”將在這裏上演壹出好戲!
李定國大軍抵達衡州後,尼堪也在二十天後姍姍來遲,抵達湘潭。駐防在湘潭的是堪稱“永歷三大勁旅”之壹的馬進忠部。(另外兩支分別是忠貞營和郝搖旗部。)
不過,經多年鏖戰,又失去堵胤錫的庇護,這支勁旅早已風光不再。尼堪來勢兇猛,馬進忠決定不吃眼前虧,果斷避其鋒芒,退守寶慶。
有狼自遠方來,不亦射乎!李定國早就給這位遠道而來的“客人”準備了壹份大禮!
十壹月二十二日,尼堪率軍進抵衡州城外三十裏,李定國派壹千多軍隊迎戰,嚴令“只許敗,不許勝,務必壹路敗退”。——看出來了,這是“誘敵深入、聚而殲之”的老套路。
不錯!“戰神”李定國精心謀劃的,確實是歷史上早已被用得爛熟的把戲。如果尼堪有點智商,李定國或許還有機會舊瓶裝點新酒,陡增波折與懸念。但是,尼堪實在太不給力,整個戰役就是壹個老得掉渣的過程,就算我有耐性講,估計也沒人有興致聽。
直接說結果吧:陷入重圍的清軍幾乎全軍覆沒,主將尼堪陣亡,貝勒屯齊率殘部艱難突圍,狼狽逃回長沙,史稱“衡州大捷”。
從永歷六年(1652年)五月至十壹月,“戰神”李定國只用了半年的時間,便相繼取得“靖州大捷”、“桂林大捷”、“衡州大捷”,掀起了南明抗清鬥爭的新高潮!
這三次大捷,不僅幹掉清廷的兩個王(定南王孔有德、敬謹莊親王尼堪),還打破了清軍不可戰勝的神話,更是沈重打擊了八旗兵不可壹世的囂張氣焰!
時任清廷吏部尚書的固山額真朱馬喇在壹封奏疏中,“痛心疾首”地承認:“自國家開創以來,未有如今日之挫辱者也。”面對如此殘酷的現實,順治皇帝也不得不哀嘆:“我朝用兵,從無此失。”
這三次大捷,發出了南明抗清的最強音,為飽受清廷暴政壓迫的百姓出了壹口惡氣,極大地鼓舞了全國抗清軍民的士氣!
勝利,是最響亮的集結號。在廣東、廣西、江西等地,很多抗清武裝曾遭到清軍的殘酷鎮壓而偃旗息鼓。在三次大捷的感召下,這些武裝又重新高舉義旗,加入到了轟轟烈烈的抗爭之中。
值得壹提的是,早已對南明小朝廷失去信心、選擇“潛水”的前明遺臣認為中興有望,也紛紛“浮出水面”,主動與“戰神”李定國取得聯系,表示願意為朝廷效力。雖然這樣的人很多是十足的政治投機分子,但抗清勢力能成為投機的對象,確實反襯了“乾坤扭轉”的勢頭。
隱居浙江的黃宗羲後來評價說:“逮夫李定國桂林、衡州之捷,兩蹶名王,天下震動,此萬歷以來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。”
如此驕人戰績,“戰神”李定國確實居功至偉!
稍微回憶壹下南明的歷史,我們便能體悟到,李定國的三次大捷,還有壹層更深的寓意——“戰神”並非神話,只要南明自己不折騰、不膽怯、不內訌,任何強敵都是可以戰勝的!
幾年來,慘敗的血腥教訓、勝利的刺眼光芒,無時無刻不在提醒南明的君臣頓悟這條克敵制勝的秘訣。但是,處處充斥著貪欲的小朝廷實在是無可救藥。
三次大捷之後,多災多難的南明再壹次坐上了“過山車”,形勢很快便急轉直下!
同臺競技
眼看“戰神”打得相當出色,孫可望開始不樂意了。
孫可望這些年在雲南、貴州勵精圖治,“政績”頗豐,深藏於內心的私欲也逐漸膨脹。按照大西軍將領原定的盟約,孫可望、李定國、艾能奇、劉文秀四人地位相當,“每公事相會,四人並坐於上”。雖然孫可望有最終的裁決權,但作為大西南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,孫可望越來越不習慣與人分享“權力盛宴”。
麻煩的是,這四個人“各領壹軍不相下”。就軍事實力而言,孫可望最多與劉文秀並列第三,跟李定國、艾能奇那是沒法比。在這種情況下,老大想吃獨食,還真不是壹件容易的事。
“幸運”的是,艾能奇在陰溝裏翻了船,提前結束“革命生涯”。劉文秀在四川沈不住氣,吃了敗仗,讓孫可望找到借口,提前結束“政治生涯”。哢擦掉兩個之後,孫可望“壹手遮天”的障礙,就只剩下李定國壹個。
堪稱“戰神”的李定國,從來就不是壹盞省油的燈。
在張獻忠的四個“義子”中,李定國實力最強、最能打仗,但最大的缺點是不善於討好領導,讓生性狡猾、善於溜須拍馬的孫可望鉆了空子。
孫可望被擁戴為“盟主”,比較顧全大局的李定國雖然不至於耿耿於懷,但對狡猾的孫可望,始終是睜大倆眼睛盯著的。
陳邦傅派胡執恭送來偽造的“秦王”敕印時,孫可望準備將錯就錯,李定國卻是“火眼金睛”,“心疑其偽”,遊說劉文秀壹起抵制。
不管是真是假,“被封公”的劉文秀看到孫可望封王,早憋了壹口氣,因此說得也很直白:“我等自為王耳,何必封!”李定國稍微委婉壹點:“我等無尺寸之功,何敢受朝廷之封。”
三個人沒談攏,孫可望卻壹意孤行,執意受封。劉文秀不敢跟孫可望對著幹,也違心地接受敕印,唯獨李定國毫不妥協,將敕印撂在壹邊。
楊畏知帶著“平遼王”的敕印回到昆明後,孫可望大為光火,拒絕受封。李定國又串通劉文秀,跟孫可望對著幹,“議欲受封”。孫可望怒了:妳們成心的是不是?(汝前不受封,今何為而受乎?)
有專制必然有反抗,孫可望與李定國的矛盾多了去了,也不必細數。即便如此,兩人還能待在壹起混,不能不說是得益於李定國的顧全大局。另外,想抗清的孫可望不能沒有“戰神”李定國,也是壹個重要的因素。
隨著李定國在湖南、廣西“壹鳴驚人”,孫可望對李定國的倚重,已經被“羨慕嫉妒恨”所代替。
李定國是孫可望派到湖南抗清的,但由於李定國打得太漂亮,“人氣”立馬就壓過了孫可望。眼看這個跟自己“若即若離”的屬下功高震主、聲名遠揚,孫可望坐不住了。
私欲戰勝了理智,會使人做出意想不到的事情。
衡州戰役時,擔心李定國“錦上添花”的孫可望開始混蛋,暗中下令配合李定國作戰的馮雙禮拆臺,致使屯齊得以率殘部突圍。
除此以外,孫可望還親自率軍入湘,跟李定國“同臺競技”。——“北兵本易殺”,妳能打,老子也能打!
永歷六年(1652年)十壹月初壹,孫可望率大軍進抵沅州,又派白文選率五萬人進攻辰州這塊“硬骨頭”,打壹個“開門紅”給天下人看看。——李定國啃不動,老子孫可望來啃!
白文選不辱使命,於十壹月二十二日拿下辰州,擊斃清軍守將徐勇。孫可望氣焰更加囂張,公然在沅州擺起“鴻門宴”,以召開“軍事會議”為名,誘捕李定國。
按照原定作戰計劃,馮雙禮、李定國、孫可望作為三個梯隊,分批入湘抗清。因此,孫可望在沅州召集軍事會議,李定國並沒有過多懷疑,趕緊率部啟程。
不過,孫可望在湖南盡在掌控之中的情況下揮師入湘,李定國心裏多少還是有些忐忑不安。為了保險起見,李定國派心腹龔銘先行出發,到沅州打前站,探聽孫可望的虛實。
盡管孫可望有意遮掩,但敏感的龔銘還是發現了壹些端倪。他推斷,沅州要舉行的不是壹次討論湖南戰事的“軍事會議”,而是壹場針對李定國的“軍事審判”!
永歷七年(1653年)正月,李定國走到武岡州,接到了龔銘從沅州送來的密信。李定國明白了,孫可望這是要“逆天”!慶幸躲過災禍之余,“戰神”李定國不禁仰天哀嘆:“本欲共圖恢復,今忌刻如此,安能成功乎!”
混蛋的孫可望想“逆天”,李定國決定忍辱負重、顧全大局。——惹不起,總還躲得起吧?!
為了避免上演“同室操戈”的慘劇,李定國率部調轉方向,於二月經鎮峽關進入廣西發展,並重新占領梧州。
李定國離開湖南後,清軍更加肆無忌憚。三月十七日,在衡州戰役中僥幸得脫的屯齊率部進攻寶慶,孫可望率援軍前來迎戰。
由於壹心想“親立大功,以服眾心”,急於求成的孫可望遭遇慘敗,致使寶慶失守。顏面盡失的孫可望撤回貴州,湖南再次陷入僵持狀態。
寶慶失利並沒有讓孫可望警醒,他還想繼續“逆天”。
探知到李定國駐防柳州後,孫可望又派馮雙禮率三萬人前往襲擊。李定國繼續顧全大局,主動後撤。不知好歹的馮雙禮窮追不舍,忍無可忍的李定國奮起還擊,懷著相當復雜的心情,將曾與自己在湖南並肩作戰的馮雙禮打得抱頭鼠竄。
挨了壹頓痛扁,孫可望才算是老實了,不敢再去廣西找李定國的茬。
從現在開始,孫可望與李定國實際上已經分道揚鑣了。
“戰神”壹戰廣東
進入廣西以後,李定國並沒有跟線國安、馬雄、全節三鎮總兵率領的“還鄉團”糾纏,而是揮師東向,對準尚可喜、耿繼茂盤踞的廣東殺了過來。
永歷七年(1653年)三月,李定國率部殺入廣東,壹路上銳不可當,二十五日便進抵肇慶,又分兵占領四會、廣寧等地。
廣東再次出現南明的正規軍,很多“潛水”的抗清武裝紛紛“冒泡”。在這些地方抗清勢力中,郝尚久是比較有故事的。
郝尚久是李成棟的部將,這些年壹直在“跳槽”。崇禎十七年(1644年),郝尚久跟隨李成棟降清。永歷二年(1648年),郝尚久又跟隨李成棟反水歸明。永歷四年(1650年),尚可喜、耿繼茂南下廣東,鄭成功也到潮州地區“武裝征糧”,兩頭受氣的郝尚久再次向清軍投降。
郝同學頻繁“跳槽”,連清軍都看不下去了,認為他反復無常、桀驁不馴,有必要進行職業素養教育。永歷六年(1652年)八月,潮州總兵郝尚久接到新任命,調任廣東水師副將。
兵種要換,地盤要占,兵權要收,還官降壹級!——早知如此,還投個屁的降!
郝尚久拒絕接受任命,死賴在潮州積極準備反水。李定國大軍開進廣東,郝尚久緊跟著又“跳槽”了,並跟李定國取得聯系。
尚可喜、耿繼茂急眼了:西面是李定國,東面是郝尚久,廣州成了“三明治”!
其實,尚可喜的擔心有點多余,廣州被兩面夾擊,郝尚久卻是被四面夾攻。西面是盤踞廣州的尚、耿大軍,東面是駐防福建漳州的清軍,北面還有占據大埔、鎮平(今廣東蕉嶺)、程鄉(今廣東梅縣)的清軍吳六奇部,甚至南面的大海也不省心,時刻得提防著鄭成功這個“武裝乞丐”來“化緣”。
李定國當然想夾擊廣州,但郝尚久明顯拿不出手,唯壹靠譜的同盟,是活動在福建沿海的鄭成功。
如果鄭成功能率水師到廣東參戰,這盤棋顯然就走活了。尚可喜、耿繼茂根本就不是兩路大軍的對手,拿下廣州不過是時間問題。
奪取廣州,孫可望占據的雲南、貴州便可通過李定國控制的兩廣,與鄭成功、魯監國活動的福建、舟山連成壹片,形成西南、華南、東南“三南並舉”的局面。
夢想鼓舞人心,現實卻令人扼腕。——李定國謀劃得很到位,但鄭成功似乎對廣東興趣不大。
鄭成功到底怎麽想的,李定國並不清楚,但肇慶就在眼前,不打壹打,實在對不起如坐針氈的尚可喜。
三月二十六日,李定國大軍開始攻城,清總兵許而顯據城固守,雙方展開攻防激戰。
肇慶的許而顯比辰州的徐勇還要難對付,他不僅兵力較強,而且鬼主意多。看到南明軍架梯攀城,許而顯暗中派精兵出城迎戰,主要的任務是搶奪南明軍的雲梯。
梯子被“收繳”,李定國另出妙計——“上天”不行,咱就“入地”。於是,數萬南明軍成了“工程兵”,除了少數警衛以外,全都忙活著壹件事——挖地道。
雖然李定國在“工地”四周都拉上了帷幕,但城墻上的許而顯站得高看得遠,很快就發現了南明軍的新戰術。許而顯見招拆招,也開始在城墻內挖攔阻溝。
許而顯的“工程”有城墻擋著,李定國看不見,繼續搞自己的“人防工程”。兩支“施工隊”在肇慶幹得不亦樂乎,廣州的尚可喜卻坐不住了。他不知道許而顯能撐多久,更不知道自己能否撐得住。孔有德、尼堪都成了“戰神”李定國的刀下之鬼,尚可喜不希望成為第三個。
心虛膽寒的尚可喜壹面向清廷請援,壹面親自帶著援軍前往肇慶。耿繼茂沒跟著來,而是在三水設防,阻擊李定國派出聯絡郝尚久的部隊,謹防兵力空虛的廣州遭到偷襲。
尚可喜抵達肇慶後,於四月初八命大軍殺出城去,迅速擊潰李定國的警衛部隊,占領各地道口,接著以煙熏的方式消滅地道內的南明軍。此時,李定國的“施工隊”還在地道裏專心作業,出又出不來,有力沒處使,很多都被熏成了“臘肉”。
李定國被迫率部撤退,距離肇慶五裏下營,尚可喜乘勝追擊,壹舉沖破南明軍的臨時阻擊陣地,大獲全勝。南明軍敗局已定,李定國見奪取肇慶已成泡影,只能撤回廣西,整軍再戰。
大軍壹撤,郝尚久就慘了。
五月,駐防南京(清廷更名為江寧)的昂邦章京哈哈木、梅勒章京噶來道噶奉命率軍增援廣東。
援軍顯然來晚了,肇慶戰役早已結束。
總不能白跑壹趟吧?李定國撤回廣西,哈哈木的“牛刀”只能用來“殺雞”了。八月十三日,耿繼茂、哈哈木會同南贛的孔國治包圍潮州,郝尚久恐怕難逃此劫。
其實,早在李定國肇慶兵敗時,郝尚久就預感到形勢不妙,病急亂投醫,趕緊向“老冤家”鄭成功請援。鄭成功倒是很積極,於六月應邀而至。
但是,老鄭“三招不離本行”,他不是來幫忙,而是來“征糧”的。——餓死鬼投胎,沒辦法。
八月,鄭成功的“援軍”滿載糧食返回福建,郝尚久被徹底拋棄了。九月十四日,潮州失守,郝尚久自殺。
“戰神”再戰廣東
第壹次進軍廣東失利後,李定國認真總結了經驗教訓,並積極籌備第二次進軍廣東。
毫不誇張地說,這是南明實現“翻盤”的最佳時機!
其壹,前面說過,廣東是永歷政權實現“三南並舉”的最關鍵壹環。
其二,常年從事海外貿易的廣東經濟發達,稅賦是廣西的十倍以上,可以為抗清提供更加雄厚的經濟保障。
其三,也是最重要的,從雙方的態勢來看,廣東雖然不至於唾手可得,但也並非難事。
我們先分析壹下清、南明雙方的力量對比情況。
——清軍方面。
哈哈木、噶來道噶畢竟是來幫忙的,剿滅郝尚久之後,十月份便離開廣東。尚可喜、耿繼茂有多少人呢?兩萬?妳以為他們帶的都是“不死鳥”啊?
現實的情況是,尚可喜、耿繼茂的老部隊加起來還剩下不足五千人。盡管在當地有所補充,勉強招募到兩萬多人,但大部分“皆遊蕩之輩,俱非經戰之輩”。換句話說,不是老油條子,便是新兵蛋子。
——南明方面。
李定國入湘時的十萬大軍還剩下四萬多人(有些部隊沒有從湖南跟隨李定國到廣西發展,另有壹些戰鬥減員),很多都是大西軍時期的“老革命”,經驗豐富,英勇善戰。
鄭成功更猛,這些年在福建沿海“悶聲不響發大財”,兵力達到十萬以上,戰船上千艘,水師實力絕對是全國第壹。難怪他總是找郝尚久“打秋風”,海上又不能種地,靠著金門、廈門壹隅之地,養活這麽多人,實在是餓啊!
除了這兩只正規武裝以外,廣東各地的義師相當活躍。欽州、廉州有鄧耀等部,高州有周金湯,陽江沿海有李常榮,恩平有王興,臺山沿海有陳奇策。這些義師的前身大多是永歷政權的正規軍,普遍接受大學士郭之奇、南明兩廣總督連城璧的指揮。雖然實力有限,但由於地皮熟、人脈廣,作為“民兵”協助主力作戰還是綽綽有余的。
如此看來,真是天賜良機!
套用壹個英語句式:這個機會如此絕妙天成,以至於只會逃跑的朱由榔都看出來了!
永歷七年(1653年)九月,朱由榔派兵部職方司員外郎程邦俊趕赴廣東,向節制各地義師的郭之奇、連城璧宣諭,闡明“藩臣定國,戮力效忠,誓復舊疆”,嚴令郭之奇、連城璧務必聯絡廣東義師做好接應。
李定國派人聯絡鄭成功之後,於永歷八年(1654年)二月從柳州出發,經橫州、靈山進抵廉州,清總兵郭虎棄城而逃。南明軍相繼占領高州、雷州,廣東西部順利光復。
尚可喜、耿繼茂驚慌失措,壹面向清廷求援,壹面收縮兵力在廣州布防。廣東清軍並不經打,遠水又解不了近渴,如果不出意外的話,第二個孔有德即將在廣東誕生。
悲催的是,意外的事情再次“意外”地發生。四月,李定國患病,壹直到八月才基本痊愈。在此期間,既定的作戰計劃受到壹定影響。
不過,輕傷不下火線,重傷不進醫院的“戰神”李定國身體有恙,腦子卻不殘,依然在堅持指揮。
真正致命的意外,是鄭成功似乎“腦殘”了,居然沒動靜!
六月,稍事停頓的李定國大軍繼續向前推進,意圖奪取與鄭成功約定的會師地點——新會。同時,李定國再次派人前往廈門,催促鄭成功趕緊出兵參戰。
六月二十九日,新會戰役爆發。由於李定國身患重病,不能親臨壹線指揮,南明軍的作戰士氣受到很大影響。另外,南明軍缺乏水師助戰,打起來相當被動。壹個月過去了,近在咫尺的新會依然紋絲不動。
八月,李定國終於盼來了廈門的消息,但卻不是好消息。鄭成功使者姍姍來遲,言辭閃爍,李定國明白,援軍是徹底沒指望了。
鄭成功兩次“爽約”,看起來令人匪夷所思,其實理由很簡單。
其壹,鄭成功壹心要做福建的“土霸王”,不想插手廣東、幫別人打架,損耗自己的實力。
其二,鄭成功正在假意與清廷“和談”,趁機解決糧食問題。在這種情況下,他不想貿然出兵,打亂向清軍“征糧”的原定部署。
李定國缺乏後援,局面越來越被動。盡管陳奇策率舟師於八月參戰,控制廣州出海口,切斷了廣州與新會的聯系,但義師實力有限,南明軍的形勢依然在繼續惡化。
新會牽制著李定國的大軍,鄭成功又按兵不動,尚可喜、耿繼茂可以放心大膽地待在廣州固守待援。
十月初三,病愈的李定國親率大軍向新會發起新壹輪猛攻,地道戰、炮戰都用遍了,新會守軍依然負隅頑抗。
新會確實是塊難啃的硬骨頭,但城中的守軍日子也不好過。
由於被圍困了幾個月,城中的糧食已經消耗殆盡,餓著肚子的守軍開始向百姓伸手,“搜粟民家,子女玉帛,恣其卷掠”。到了十二月,百姓也斷了炊,從“掘鼠羅雀”到“食及浮萍草履”,將能吃的、不能吃的全吃了個遍,就差抱著城墻啃了,實在是慘不忍睹。令人發指的是,喪失人性的清軍無糧可掠,竟然戕殺居民為食!(兵又略人為脯臘,殘骼委地,不啻萬余。)
十二月初十,朱馬喇率援軍抵達廣東,十四日會同尚可喜、耿繼茂向南明軍發起總攻。四天激戰後,李定國全線潰退,除了留下幾千人鎮守羅定外,大軍主力悉數撤回廣西,第二次進軍廣東以失敗告終。
次年正月,羅定守軍撤回廣西。二月,李定國在清軍的追擊下退往南寧,南明“三南並舉”的重大轉機化為泡影。
失去孫可望的支持和鄭成功的協同,閃耀在“戰神”李定國頭上的光環,也開始黯然失色。
孫可望比較強悍地整頓四川、貴州,比較無恥地收拾永歷朝廷,最初的動機其實比較單純,那就是執行張獻忠“爾急歸明,毋為不義”的臨終托付,壹門心思抗清。
抗清,必須有統壹的領導,不服氣的要摁住(李定國、劉文秀)、不聽話的要收拾(四川、貴州軍閥)、沒本事的靠邊站(永歷君臣),這就是孫可望的邏輯。
南明這麽多年的歷史證明,清軍很多時候喜歡“不請自到”。當孫可望壹面經營西南、壹面為“請封”跟永歷朝廷慪氣時,北京方面有了新動向。
永歷六年(1652年)二月,吳三桂、李國翰奉順治皇帝的命令(多爾袞在前壹年底病死),率軍自漢中入川,進抵保寧。
吳三桂率幾萬大軍奉命前來,顯然不是幫著李國英守保寧,而是意圖進取四川的。由於孫可望正在貴州集結兵力準備入湘,留在四川的留守部隊並不多,因此吳三桂的進攻速度相當快。
吳三桂率軍自保寧南下,先清剿川西的孫可望勢力。二十二日,清軍進抵成都,守將林時泰兵力單薄,不戰而降,被清軍處死。二十五日,嘉定失守。
三月,清軍向川東方向運動,初五占領合州。鎮守重慶的盧明臣也沒多少人,於十四日棄守重慶,主動後撤。四月,川南的敘州告急,守將白文選也選擇了主動後撤,退往永寧。隨後,清軍在四川攻城略地,將孫可望的勢力剿滅或者驅逐殆盡。
孫可望想到清軍會來,但沒有想到來得如此迅速,趕緊派劉文秀部署入川抗清。
狹路相逢勇者勝!與不可壹世的清軍壹決雌雄的時刻終於到了!
孫可望、李定國、劉文秀、艾能奇,張獻忠手下的這四員猛將,個頂個的打架天才,都不是吃素的貨。
“老大”孫可望的本事,我們已經見識過了,西南三省不是吹出來的,是實實在在打出來的!艾能奇轉戰千裏、戰功顯赫,最後在雲南“剿匪”時,陰溝裏翻了船。
現在,終於輪到劉文秀上場了!
大腕出場,不同凡響,劉文秀率部入川果然是大手筆。劉文秀帶著四萬多人,不是選擇壹個方向入川,而是兵分三路,從川西南的建昌、川南的永寧、川東南的彭水同時推進。
敢這樣入川打架的,迄今為止獨此壹人!
劉文秀的靈魂深處,有壹股不服輸的勇氣,更有壹股舍我其誰的傲氣!
八月初九,中路軍率先告捷,全殲鎮守敘州的清軍,並會合白文選部反攻重慶。同時,西路、東路也秋風掃落葉,快速向北推進。
吳三桂嚇傻了:雖說出來混遲早要還,這還得也太快了吧?
八月十九日,清軍在四川的“三巨頭”——吳三桂、李國翰、李國英在夾江開了壹次重要會議,會議做出了壹個極其重要的決定——撤!
大家都是聰明人,都明白“打得贏就打,打不贏就跑”的道理。“撤退”的共識很快達成,但分歧在於:撤到哪裏去?
三個人,兩種意見:A.四川保寧;B.陜西漢中。
李國英選A。——幾萬大軍壹拔腿就撤到陜西,我這個四川巡撫怎麽向朝廷交代?
吳三桂、李國翰選B。——多說無益,安全第壹。妳怎麽交代是妳的事,妳的事關我們屁事?
二比壹,少數服從多數,開溜!
“夾江會議”的決定很快傳達到分散在四川各地的清軍,大家接到命令便拔腿開溜,向陜西方向撤退。
各路清軍跑得不亦樂乎,只有重慶的清軍比較悲催。
當時,駐紮在重慶的清軍將領有壹大幫子,包括梅勒章京葛朝忠、白含真、佟師聖、鑲紅旗章京尹得才、永寧總兵柏永馥、左路總兵陳德、夔州總兵盧光祖等等。接到吳三桂的命令後,諸將領趕緊率各部後撤。
八月二十五日,劉文秀會合白文選的部隊進抵重慶,突然發現很不對勁:清軍死哪兒去了?
雖然各地軍隊都發現清軍在後撤,但重慶的清軍“不翼而飛”,讓劉文秀有點如鯁在喉的感覺,這跟他入川的重大使命有很大關系。
什麽重大使命?不是抗請嗎?——對,但不全對!除了清剿吳三桂、李國翰、李國英以外,劉文秀還肩負壹項重任:打通川鄂通道,為將來順江東下掃清障礙。
這條抗清的道路,富有遠見的孫可望已經盤算很久了。就目前的形勢來看,如果單純采用“推土機”戰術,從貴州經湖南、江西、浙江,壹路推到南京,難度顯然是相當大的。但要是控制了長江這條“黃金水道”,進軍南京的難度至少可以打個對折。
顯然,重慶的守軍“人間蒸發”,對於長江水道的暢通,隱患是相當大的。因此,劉文秀不敢怠慢,趕緊率軍日夜兼程向北追擊。
二十八日,在距離重慶壹百多裏的停溪,劉文秀的追兵終於看到了清軍的影子,隨即像餓綠了眼的惡狼見到肥肥的綿羊壹般撲了上去。葛朝忠等人哪裏想到會臨時加上這出戲,登時驚慌失措、亂作壹團,成了劉文秀大軍的活靶子。
最後,壹大群將領中只有永寧總兵柏永馥僥幸得以保全,帶著幾百殘兵敗卒,踉踉蹌蹌逃至保寧。
劉文秀帶著幾萬大軍在四川各地窮追猛打,招架不住的清軍紛紛後撤,四川的局面基本上又回到了戰前狀態。
“衰神”之保寧之戰
九月十壹日,吳三桂、李國翰、李國英撤到綿州(今四川綿陽),接著又撤往川、陜邊境的廣元。眼看就要進入陜西境內,李國英屢次反對無效,但保寧終於有人看不下去了。
看不下去的人,是時任四川巡按禦史的郝浴。當時,郝浴帶著總兵嚴自明鎮守保寧。雖然有個總兵在身邊,但這個總兵充其量算個連長,手下就壹百來號人,實在是悲慘到了極致。
吳三桂、李國翰二話不說準備撤回陜西,郝浴便頻繁派人給吳三桂帶話,好言相勸之余也不乏恫嚇威脅:奉旨入川,卻棄守四川,這可是欺君之罪!奉勸妳出川之前,先摸壹摸自己有幾個腦袋,免得徒增“早知今日,何必當初”的哀嘆,毀壹世英名於壹旦!
李國英反對,吳三桂可以充耳不聞,但郝浴出聲,吳三桂必須掂量掂量,他知道這個“奉旨告禦狀”的禦史不好惹。
從吳三桂入川起,郝浴的彈劾奏疏就沒有斷過,今天告他“驕恣部下、淫殺不法”,明天告他“殘暴無紀律”。雖然朝廷沒有把手握重兵的吳三桂怎麽樣,但確實讓吳三桂不厭其煩。
“好鞋不踩臭狗屎”,吳三桂經過壹番深思熟慮,還是改變了決定,率領後撤大軍於九月十九日折返保寧。
此後,郝浴算是跟吳三桂扛上了,屢次上疏彈劾。吳三桂屁股也不幹凈,每次都被點到要害。被踩了尾巴的吳三桂絕地反擊,兩人吵得烏煙瘴氣。“欺軟怕硬”的順治皇帝不想攬這筆爛賬,索性將郝浴流放到關外了事。直至吳三桂造反,郝浴才得到赦免,重返官場。
劉文秀率軍入川,用了不到兩個月,便將清軍打回原形,保寧恐怕也難以保全。但是,隨著吳三桂、李國翰、李國英返回保寧,川北的形勢發生了變化。更要命的問題是,壹路凱歌高奏的劉文秀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。
驕兵必敗,這是壹個極其危險的信號,劉文秀很快就會變成“衰神”!
在劉文秀看來,收復全川只剩下最後壹步。不動則已,動則不留遺憾,劉文秀決定畢其功於壹役。
十月初二,劉文秀率大軍進抵保寧,將固守的清軍團團圍困。
客觀地說,劉文秀乘勝進攻保寧,算不上戰略失誤,畢竟自己掌握著整個四川戰場的主動權。但是,靈魂深處的傲氣、輕而易舉的勝利,讓劉文秀失去了必要的理智與穩重。
他忽略了壹個至關重要的現象:大軍壹路攻城略地,收復了保寧以外的四川全境,但消滅的清軍並不多!
除了重慶以外,四川各地的清軍大部分都不戰而逃、“人間蒸發”。這些人去了哪裏?顯然,答案有且只有壹個——保寧!
各地清軍退守保寧,再加上吳三桂、李國翰親率的部隊入城,保寧清軍的實力已經不可小覷。在兵力不占絕對優勢的情況下,劉文秀不經細致準備,便貿然組織對保寧的進攻,戰略上是相當失策的。
戰略上的重大失誤,或許是因為劉文秀情報不明,又掉以輕心,似乎還情有可原。但是,劉文秀急於剿滅清軍的有生力量,在戰術上犯了壹個相當沒有技術含量的低級錯誤——“鐵桶戰術”。
大軍進抵保寧後,劉文秀將保寧包圍得水泄不通,並從各個方向向城內固守的清軍發起全面攻擊。
這個戰術似乎沒有什麽問題,當年堵胤錫率領忠貞營圍攻長沙,也是這麽幹的。要不是何騰蛟瞎攪和,拿下長沙也就是壹兩天的事情。這麽強悍的戰術,到了劉文秀這裏,怎麽就成了低級錯誤呢?
打仗是門技術活,具體問題得具體分析,生搬硬套是要不得的!
——“鐵桶戰術”的前提是對敵形成壓倒性優勢,但隨著保寧的清軍得到大量補充,劉文秀的這種優勢蕩然無存。
——保寧跟贛江壹樣,也是三面環水,不過是由嘉陵江彎成“U字形”形成的,東、西、南三面被江水阻隔,易守難攻。
在這種情況下采取“鐵桶戰術”,對於壹個身經百戰的將領而言,確實是不可原諒的。
戰略失誤,戰術繼續失誤,“衰神”劉文秀的敗局不可避免。
十月十壹日,劉文秀率五萬軍隊從四面攻城,主攻是沒有河流阻隔的北面,並將嘉陵江上的浮橋全部砍斷,企圖將吳三桂、李國翰困死在保寧。
插翅難逃的吳三桂絕地反擊,對準劉文秀大軍中最薄弱的張先璧部發起猛攻。張先璧潰敗,沖散了毗鄰的王復臣部,劉文秀大軍陷入壹片混亂之中。吳三桂、李國翰趁機采取“亂棍戰術”,更是亂上加亂。
由於三面河流上的浮橋被砍斷,劉文秀大軍陷入了絕地,遭遇慘敗,王復臣、姚之貞等將領陣亡,劉文秀率余部撤回貴州境內。孫可望念其勞苦功高,只是解除兵權,送回昆明賦閑;對後來歸附的張先璧就不必客氣了,直接命人拖出去亂棍打死。
躊躇滿誌的劉文秀敗得壹塌糊塗,四川又落到了清軍的手裏;勉強留守的吳三桂勝得稀裏糊塗,也不敢貿然擴大戰果。自此,四川轉入僵持狀態,孫可望打通川鄂水道的設想落空,成為壹大憾事!
“戰神”之靖州大捷
四川意外失手,但湖南卻有意外的驚喜。
入湘抗清,孫可望已經盤算好幾年了。早在永歷五年(1651年)四月,孫可望便派部將馮雙禮作為“開路先鋒”,率四萬多人(包括騎兵壹萬多,還有戰象十余頭)進入湖南境內。
有意思的是,清軍“三王”南下兩廣,七拼八湊才攢足四萬人。孫可望打湖南壹個省,光是“開路先鋒”就不止四萬,還有大象助陣,這排場可真夠大的!
跟南明政權交鋒的幾年來,清軍似乎只有受降的時候才見過這麽多人!
馮雙禮率領的這支“先鋒部隊”從貴州出發,於四月十五日進抵湖南沅州。清軍在沅州的守軍有多少呢?
三千人!
沅州之戰,就是壹場“要妳命三千”的殺人遊戲。毫無懸念,搞“鐵桶戰術”的馮雙禮初戰告捷,清軍守將鄭壹統、知州柴宮桂被俘獲。
馮雙禮的第二站是沅州北面的辰州,駐守在此的是清軍辰常總兵徐勇。徐勇是個相當抗打的貨,帶著幾千人精心布置防線,扼險固守、負隅頑抗,人生地不熟的馮雙禮沒能打下來。
老馮沒有劉文秀的傲氣,能夠比較坦然地接受現實。既然奉命打整個湖南,有足夠的空間發揮和表現,沒必要計較壹座孤城的得失。
辰州的徐勇松了壹口氣,輪到駐守寶慶的沈永忠抑郁了。
為了解除孔有德南下的後顧之憂,他被清廷從山東調到湖南修“爛尾樓”。壹年多來,沈永忠帶著兩萬人轉戰湖南各地,跟各式各樣的“釘子戶”鬥智鬥勇。如今“釘子”沒拔完,又闖進四萬人來搶飯碗,沈永忠實在是欲哭無淚。
憑借做了壹年多“東道主”的“主場”優勢,沈永忠帶著兩萬人與馮雙禮的四萬大軍艱難周旋。雙方妳來我往,各有勝負,湖南很快便進入僵持狀態。
吳三桂、李國翰奉命率軍到四川撒野,並沒有改變孫可望進軍湖南的既定計劃。
馮雙禮的四萬人不過是“開路先鋒”,那麽進取湖南的主力是誰呢?前面說過,在整個南明時代,能把清廷打急眼的只有兩個人,壹個是在陜西點火燒後院的姜瓖,另外壹個,便是堪稱南明“戰神”的原大西軍安西將軍——李定國。
有點可惜,輪到“戰神”出場的時候,多爾袞已經死翹翹了,急眼的人變成了親政不久的順治皇帝福臨。
永歷六年(1652年)四月,“戰神”李定國率十萬大軍進入湖南,戰場的力量對比發生逆轉。
五月中旬,李定國會合馮雙禮部進攻靖州。沈永忠此時還不知道李定國大軍已經入湘,誤以為又是馮雙禮在找茬,便派麾下總兵張國柱率八千兵馬前往靖州支援。
幾天之後,李定國大軍取得“靖州大捷”,遍體鱗傷的張國柱逃回寶慶。沈永忠清點了壹下人數,還剩下兩千多人,立馬傻眼了:妳是打架去了,還是集體自殺去了?
張國柱對作戰經過做了壹番描述,沈永忠聽得毛骨悚然。他敏銳地感覺到,這次在靖州鬧騰的並不只是馮雙禮的部隊。
看來,孫可望開始對湖南下狠手了!
沈永忠只猜到孫可望非拿下湖南不可,卻怎麽也沒想到,自己的對手會是南明最強悍的“戰神”李定國。
湖南危急,沈永忠能想到的最佳辦法,就是趕緊派人到桂林,懇請孔有德回師救援。
救,還是不救?
孔有德不需要權衡商議,更不需要扔硬幣,在第壹時間便給出答復:沒空!
孔有德如此絕情,打醬油的都看不下去了。要不是幫妳把守後院,老沈也不會大老遠被調過來接這個爛攤子。如今老沈落難,妳老孔竟然見死不救,未免太不仗義了吧?
圍觀群眾往往都是不明真相的,其實孔有德有足夠的理由拒絕:
其壹,報沈永忠的“壹疏之仇”。
進軍廣西後,由於後勤補給壹時跟不上,孔有德曾經向衡州、永州借支糧餉,並承諾有借有還。屁大點事,沈永忠卻壹封奏疏捅到朝廷上去,搞得孔有德十分難堪。
其二,沈永忠謊報軍情。
孔有德判斷,廣西有自己的大軍坐鎮,孫可望不可能派大部隊進入湖南,除非他的雲南、貴州不想要了。因此,壹定是沈永忠自己沒本事,打了敗仗就怪對手太強悍。
其三,兵力難以在短時間內收攏。
孔有德雖然坐鎮省會桂林,但三鎮總兵分別鎮守在廣西各地,線國安駐南寧、馬雄駐梧州壹帶、全節駐柳州(原配屬的曹得先、馬蛟麟兩位總兵已調離),收攏起來相當麻煩。
其四,大軍北撤,廣西怎麽辦?
根據以往的經驗,清軍撤離之後,各種抗清勢力比雨後春筍冒得還要快。兩萬大軍回援湖南,能否幹掉李定國、馮雙禮還很難說,就算幹掉了,妳沈永忠還能重新把廣西拿下來嗎?
說壹千道壹萬,各端各的碗、各吃各的飯。李定國在湖南,歸妳沈永忠管。他敢打到廣西,我負責收拾,不用妳沈永忠摻和。(設警逼我境,自有區處。)
救兵搬不來,打又打不過,所幸沈永忠還剩下壹條路——跑!
從寶慶北撤這壹路,沈永忠是食不甘味、夜不能寐。在他看來,至少有兩個人會要他的命:壹是李定國,壹是順治帝。
李定國的追兵容易躲,大不了多走幾天山路而已。如果順治帝要追究“失地之罪”,沈永忠擺什麽姿勢都要中槍。
沈永忠膽戰心驚地走到湘潭,接到了順治帝下達的密旨——“不可浪戰,移師保守”,壹切都妥了!
奉旨撤退,再沒有比這更愜意的事情了!
有了這道“護身符”,沈永忠跑得飛快,也撤得相當徹底。六月初二進入長沙後,索性壹不做二不休,於八月初六主動棄守省會,退往嶽州。
沈永忠跑了,湖南各地的官員、武裝也紛紛“樹倒猢猻散”,開展“逃跑大比拼”。很快,除了嶽州、常德、辰州以外,李定國已收復湖南絕大部分地域。
“戰神”之桂林大捷
四川打得只剩下壹個保寧時,“衰神”劉文秀沈不住氣,結果骨頭沒啃下來,倒把門牙崩壞了兩顆,被孫可望打發回昆明“休假式療養”去了。此時的湖南還剩下三座城池,李定國卻決定“見好就收”。——是否具有敢於舍棄的遠見與胸懷,往往決定著能力水平的高低!
湖南可以先放壹放,李定國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辦——收拾孔有德!
此時,孔有德還在做著他的“春秋大夢”,認為湖南的局面不足為慮。盡管湖南各地相繼被李定國的軍隊收復,孔有德除了在五月底派壹部兵力駐守全州“警戒”以外,再未作更多的防備。
六月二十八日,李定國率大軍自武岡、新寧進攻全州,原駐防軍加上派來“警戒”的清軍被“壹鍋端”。戰報傳來,孔有德大為震恐,次日親率桂林的留守部隊趕赴嚴關防禦。
李定國乘勝進抵嚴關,將清軍揍得七葷八素,孔有德當天便倉皇撤回桂林固守。六月三十日,李定國的前鋒部隊進抵桂林郊外。七月初二,桂林陷入重圍,孔有德趕緊派人通知線國安、馬雄、全節,令三鎮總兵火速回援桂林。
桂林危在旦夕,三鎮總兵又不是空軍。回援之路要壹步壹步地走,而壹切都已經太晚了!
七月初四,李定國率軍攻破桂林,悔恨交加的孔有德選擇了自盡,史稱“桂林大捷”。茍且偷生於桂林城內的陳邦傅、王荃可、張星光等降清大臣被活捉,並於九月在貴陽伏誅。其中,惡貫滿盈的操蛋分子陳邦傅受刑待遇最高——剝皮揎草,傳示滇黔!
幹掉孔有德不是唯壹目標,奪取桂林更不是終點,“戰神”李定國繼續率軍南下。孔有德自行了斷後,輪到線國安、馬雄、全節傻眼了:主將都嗚呼哀哉了,還打個鳥仗?
三鎮總兵壹溜煙撤到梧州,李定國在廣西收復失地,忙得不亦樂乎。八月,終於騰出手來的李定國向梧州推進,線國安、馬雄、全節不戰自潰,逃往廣東投奔了尚可喜。
八月十五日,李定國占領梧州,廣西至此全部光復。四個月的時間,“戰神”壹舉拿下兩個省!
尚可喜曾經遭到孔有德的恥笑,如今孔有德死這麽慘,尚可喜實在是沒有幸災樂禍的雅興。不是老尚胸懷寬廣不記仇,而是李定國的大軍太強悍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話,自己很快就會成為下壹個孔有德。
令人大跌眼鏡的是,尚可喜臆想的“意外”,偏偏意外地發生了。
李定國的大軍已經在廣西邊境的梧州集結,準備揮師向東收拾尚可喜,卻接到了孫可望的命令——火速回援湖南!
回援湖南?那裏出了什麽狀況?莫非沈永忠“原地滿血復活”還“裝備升級”?
怎麽可能!沈永忠壹直都是半死不活。真實的情況是:湖南來了“新客”——清敬謹莊親王尼堪。當然,尼堪不是單刀赴會,而是帶著幾千八旗精兵來的。他也不是來觀光的,而是來找人打架的。直白地說,是來給沈永忠“報仇”兼“撐腰”的。
原來,順治皇帝見湖南打得太不像樣,擔心影響兩廣的態勢,於七月十八日委任尼堪為定遠大將軍,率八旗兵南下。
按照原定計劃,尼堪率軍經湖南進入貴州,會同四川的吳三桂、李國翰搗孫可望的老巢,演壹出“螳螂捕蟬,黃雀在後”的好戲,順帶把朱由榔請到北京“把酒言歡”。
但是,尼堪走到半道上,孔有德“殉難”的噩耗便傳到了北京。順治帝趕緊在八月初五重新下達命令,讓尼堪拿下湖南後向廣西推進。
同時,順治帝又給廣東的尚可喜、耿繼茂下了壹道死命令:固守待援,保存實力,不準去廣西犯賤!(切毋憤恨,輕赴廣西;倘賊犯廣東,爾等宜圖萬全為上計。)其實,順治帝未免多慮了。尚可喜天天提心吊膽,捏雙筷子手都發抖,哪裏還敢去廣西送死。
尚可喜沒敢動,但尼堪的八旗兵距離湖南越來越近。湖南壹旦有失,貴州恐怕危矣,所以孫可望急眼了,趕緊命進軍廣西的李定國回撤。
客觀地說,家大業大的孫可望逐漸變得跟劉文秀壹個毛病——不穩重、不淡定,缺乏“泰山崩於前而面不改色”的氣魄,更缺乏“會當淩絕頂,壹覽眾山小”的戰略眼光。
基於當時的態勢來分析,孫可望的決定相當草率、相當幼稚。
其壹,李定國率大軍滯留兩廣,對清廷是壹個重要的威懾。他們擔心,兩廣壹旦有失,必然導致西南的朱由榔、孫可望與東南的鄭成功、魯監國連成壹片。因此,尼堪未必敢大舉進攻貴州,西南老巢還是安全的。
其二,尼堪大軍進入湖南尚需時日,在湖南打開局面也需要壹定的時間。李定國即使要回援,也有足夠的時間先進軍廣東,將尚可喜、耿繼茂揍得“生活不能自理”,再從容地經韶州、郴州北上迎戰尼堪。
其三,即使李定國從廣西回援,也不應全軍北上,廣西至少需要留下足以抗衡尚可喜、耿繼茂挑釁的留守部隊。李定國手握十萬大軍,留下壹半兵力守在梧州、桂林,尚可喜、耿繼茂根本不敢動,而五萬大軍收拾尼堪,顯然是綽綽有余。
遺憾的是,所有不該犯的錯誤,孫可望、李定國全犯了。十月三十日,李定國率十萬大軍回撤至衡州。
李定國大軍撤退後,新任的廣西巡撫徐天佑帶著壹兩千人鎮守梧州,安西將軍朱喜三則率領壹千多烏合之眾駐防桂林,其余各地的防守兵力更加單薄,廣西頓時空空如也。
來勢洶洶的李定國大軍突然沒了蹤跡,僥幸脫險的尚可喜膽識愈壯。為了探查廣西的虛實,李定國前腳剛走,尚可喜就令孔有德麾下的三鎮總兵線國安、馬雄、全節率部返回廣西。(順治帝曾下令尚可喜、耿繼茂不準去廣西犯賤,所以尚軍自己不敢亂動。)
九月初五,三鎮總兵占領梧州,寡不敵眾的徐天佑只得後撤桂林,又於十壹月底撤至柳州。廣西兵力如此空虛,線國安等人竟然磨蹭到十二月下旬才占領平樂。從梧州打到平樂區區四百裏,花了將近四個月,三鎮的戰鬥力也實在是爛得可以。壹直到次年正月,清軍才相繼攻取陽朔、桂林,勉勉強強“收復”了廣西。
“戰神”之衡州大捷
交待完廣西,再來說湖南,“戰神”將在這裏上演壹出好戲!
李定國大軍抵達衡州後,尼堪也在二十天後姍姍來遲,抵達湘潭。駐防在湘潭的是堪稱“永歷三大勁旅”之壹的馬進忠部。(另外兩支分別是忠貞營和郝搖旗部。)
不過,經多年鏖戰,又失去堵胤錫的庇護,這支勁旅早已風光不再。尼堪來勢兇猛,馬進忠決定不吃眼前虧,果斷避其鋒芒,退守寶慶。
有狼自遠方來,不亦射乎!李定國早就給這位遠道而來的“客人”準備了壹份大禮!
十壹月二十二日,尼堪率軍進抵衡州城外三十裏,李定國派壹千多軍隊迎戰,嚴令“只許敗,不許勝,務必壹路敗退”。——看出來了,這是“誘敵深入、聚而殲之”的老套路。
不錯!“戰神”李定國精心謀劃的,確實是歷史上早已被用得爛熟的把戲。如果尼堪有點智商,李定國或許還有機會舊瓶裝點新酒,陡增波折與懸念。但是,尼堪實在太不給力,整個戰役就是壹個老得掉渣的過程,就算我有耐性講,估計也沒人有興致聽。
直接說結果吧:陷入重圍的清軍幾乎全軍覆沒,主將尼堪陣亡,貝勒屯齊率殘部艱難突圍,狼狽逃回長沙,史稱“衡州大捷”。
從永歷六年(1652年)五月至十壹月,“戰神”李定國只用了半年的時間,便相繼取得“靖州大捷”、“桂林大捷”、“衡州大捷”,掀起了南明抗清鬥爭的新高潮!
這三次大捷,不僅幹掉清廷的兩個王(定南王孔有德、敬謹莊親王尼堪),還打破了清軍不可戰勝的神話,更是沈重打擊了八旗兵不可壹世的囂張氣焰!
時任清廷吏部尚書的固山額真朱馬喇在壹封奏疏中,“痛心疾首”地承認:“自國家開創以來,未有如今日之挫辱者也。”面對如此殘酷的現實,順治皇帝也不得不哀嘆:“我朝用兵,從無此失。”
這三次大捷,發出了南明抗清的最強音,為飽受清廷暴政壓迫的百姓出了壹口惡氣,極大地鼓舞了全國抗清軍民的士氣!
勝利,是最響亮的集結號。在廣東、廣西、江西等地,很多抗清武裝曾遭到清軍的殘酷鎮壓而偃旗息鼓。在三次大捷的感召下,這些武裝又重新高舉義旗,加入到了轟轟烈烈的抗爭之中。
值得壹提的是,早已對南明小朝廷失去信心、選擇“潛水”的前明遺臣認為中興有望,也紛紛“浮出水面”,主動與“戰神”李定國取得聯系,表示願意為朝廷效力。雖然這樣的人很多是十足的政治投機分子,但抗清勢力能成為投機的對象,確實反襯了“乾坤扭轉”的勢頭。
隱居浙江的黃宗羲後來評價說:“逮夫李定國桂林、衡州之捷,兩蹶名王,天下震動,此萬歷以來全盛之天下所不能有。”
如此驕人戰績,“戰神”李定國確實居功至偉!
稍微回憶壹下南明的歷史,我們便能體悟到,李定國的三次大捷,還有壹層更深的寓意——“戰神”並非神話,只要南明自己不折騰、不膽怯、不內訌,任何強敵都是可以戰勝的!
幾年來,慘敗的血腥教訓、勝利的刺眼光芒,無時無刻不在提醒南明的君臣頓悟這條克敵制勝的秘訣。但是,處處充斥著貪欲的小朝廷實在是無可救藥。
三次大捷之後,多災多難的南明再壹次坐上了“過山車”,形勢很快便急轉直下!
同臺競技
眼看“戰神”打得相當出色,孫可望開始不樂意了。
孫可望這些年在雲南、貴州勵精圖治,“政績”頗豐,深藏於內心的私欲也逐漸膨脹。按照大西軍將領原定的盟約,孫可望、李定國、艾能奇、劉文秀四人地位相當,“每公事相會,四人並坐於上”。雖然孫可望有最終的裁決權,但作為大西南實際上的最高統治者,孫可望越來越不習慣與人分享“權力盛宴”。
麻煩的是,這四個人“各領壹軍不相下”。就軍事實力而言,孫可望最多與劉文秀並列第三,跟李定國、艾能奇那是沒法比。在這種情況下,老大想吃獨食,還真不是壹件容易的事。
“幸運”的是,艾能奇在陰溝裏翻了船,提前結束“革命生涯”。劉文秀在四川沈不住氣,吃了敗仗,讓孫可望找到借口,提前結束“政治生涯”。哢擦掉兩個之後,孫可望“壹手遮天”的障礙,就只剩下李定國壹個。
堪稱“戰神”的李定國,從來就不是壹盞省油的燈。
在張獻忠的四個“義子”中,李定國實力最強、最能打仗,但最大的缺點是不善於討好領導,讓生性狡猾、善於溜須拍馬的孫可望鉆了空子。
孫可望被擁戴為“盟主”,比較顧全大局的李定國雖然不至於耿耿於懷,但對狡猾的孫可望,始終是睜大倆眼睛盯著的。
陳邦傅派胡執恭送來偽造的“秦王”敕印時,孫可望準備將錯就錯,李定國卻是“火眼金睛”,“心疑其偽”,遊說劉文秀壹起抵制。
不管是真是假,“被封公”的劉文秀看到孫可望封王,早憋了壹口氣,因此說得也很直白:“我等自為王耳,何必封!”李定國稍微委婉壹點:“我等無尺寸之功,何敢受朝廷之封。”
三個人沒談攏,孫可望卻壹意孤行,執意受封。劉文秀不敢跟孫可望對著幹,也違心地接受敕印,唯獨李定國毫不妥協,將敕印撂在壹邊。
楊畏知帶著“平遼王”的敕印回到昆明後,孫可望大為光火,拒絕受封。李定國又串通劉文秀,跟孫可望對著幹,“議欲受封”。孫可望怒了:妳們成心的是不是?(汝前不受封,今何為而受乎?)
有專制必然有反抗,孫可望與李定國的矛盾多了去了,也不必細數。即便如此,兩人還能待在壹起混,不能不說是得益於李定國的顧全大局。另外,想抗清的孫可望不能沒有“戰神”李定國,也是壹個重要的因素。
隨著李定國在湖南、廣西“壹鳴驚人”,孫可望對李定國的倚重,已經被“羨慕嫉妒恨”所代替。
李定國是孫可望派到湖南抗清的,但由於李定國打得太漂亮,“人氣”立馬就壓過了孫可望。眼看這個跟自己“若即若離”的屬下功高震主、聲名遠揚,孫可望坐不住了。
私欲戰勝了理智,會使人做出意想不到的事情。
衡州戰役時,擔心李定國“錦上添花”的孫可望開始混蛋,暗中下令配合李定國作戰的馮雙禮拆臺,致使屯齊得以率殘部突圍。
除此以外,孫可望還親自率軍入湘,跟李定國“同臺競技”。——“北兵本易殺”,妳能打,老子也能打!
永歷六年(1652年)十壹月初壹,孫可望率大軍進抵沅州,又派白文選率五萬人進攻辰州這塊“硬骨頭”,打壹個“開門紅”給天下人看看。——李定國啃不動,老子孫可望來啃!
白文選不辱使命,於十壹月二十二日拿下辰州,擊斃清軍守將徐勇。孫可望氣焰更加囂張,公然在沅州擺起“鴻門宴”,以召開“軍事會議”為名,誘捕李定國。
按照原定作戰計劃,馮雙禮、李定國、孫可望作為三個梯隊,分批入湘抗清。因此,孫可望在沅州召集軍事會議,李定國並沒有過多懷疑,趕緊率部啟程。
不過,孫可望在湖南盡在掌控之中的情況下揮師入湘,李定國心裏多少還是有些忐忑不安。為了保險起見,李定國派心腹龔銘先行出發,到沅州打前站,探聽孫可望的虛實。
盡管孫可望有意遮掩,但敏感的龔銘還是發現了壹些端倪。他推斷,沅州要舉行的不是壹次討論湖南戰事的“軍事會議”,而是壹場針對李定國的“軍事審判”!
永歷七年(1653年)正月,李定國走到武岡州,接到了龔銘從沅州送來的密信。李定國明白了,孫可望這是要“逆天”!慶幸躲過災禍之余,“戰神”李定國不禁仰天哀嘆:“本欲共圖恢復,今忌刻如此,安能成功乎!”
混蛋的孫可望想“逆天”,李定國決定忍辱負重、顧全大局。——惹不起,總還躲得起吧?!
為了避免上演“同室操戈”的慘劇,李定國率部調轉方向,於二月經鎮峽關進入廣西發展,並重新占領梧州。
李定國離開湖南後,清軍更加肆無忌憚。三月十七日,在衡州戰役中僥幸得脫的屯齊率部進攻寶慶,孫可望率援軍前來迎戰。
由於壹心想“親立大功,以服眾心”,急於求成的孫可望遭遇慘敗,致使寶慶失守。顏面盡失的孫可望撤回貴州,湖南再次陷入僵持狀態。
寶慶失利並沒有讓孫可望警醒,他還想繼續“逆天”。
探知到李定國駐防柳州後,孫可望又派馮雙禮率三萬人前往襲擊。李定國繼續顧全大局,主動後撤。不知好歹的馮雙禮窮追不舍,忍無可忍的李定國奮起還擊,懷著相當復雜的心情,將曾與自己在湖南並肩作戰的馮雙禮打得抱頭鼠竄。
挨了壹頓痛扁,孫可望才算是老實了,不敢再去廣西找李定國的茬。
從現在開始,孫可望與李定國實際上已經分道揚鑣了。
“戰神”壹戰廣東
進入廣西以後,李定國並沒有跟線國安、馬雄、全節三鎮總兵率領的“還鄉團”糾纏,而是揮師東向,對準尚可喜、耿繼茂盤踞的廣東殺了過來。
永歷七年(1653年)三月,李定國率部殺入廣東,壹路上銳不可當,二十五日便進抵肇慶,又分兵占領四會、廣寧等地。
廣東再次出現南明的正規軍,很多“潛水”的抗清武裝紛紛“冒泡”。在這些地方抗清勢力中,郝尚久是比較有故事的。
郝尚久是李成棟的部將,這些年壹直在“跳槽”。崇禎十七年(1644年),郝尚久跟隨李成棟降清。永歷二年(1648年),郝尚久又跟隨李成棟反水歸明。永歷四年(1650年),尚可喜、耿繼茂南下廣東,鄭成功也到潮州地區“武裝征糧”,兩頭受氣的郝尚久再次向清軍投降。
郝同學頻繁“跳槽”,連清軍都看不下去了,認為他反復無常、桀驁不馴,有必要進行職業素養教育。永歷六年(1652年)八月,潮州總兵郝尚久接到新任命,調任廣東水師副將。
兵種要換,地盤要占,兵權要收,還官降壹級!——早知如此,還投個屁的降!
郝尚久拒絕接受任命,死賴在潮州積極準備反水。李定國大軍開進廣東,郝尚久緊跟著又“跳槽”了,並跟李定國取得聯系。
尚可喜、耿繼茂急眼了:西面是李定國,東面是郝尚久,廣州成了“三明治”!
其實,尚可喜的擔心有點多余,廣州被兩面夾擊,郝尚久卻是被四面夾攻。西面是盤踞廣州的尚、耿大軍,東面是駐防福建漳州的清軍,北面還有占據大埔、鎮平(今廣東蕉嶺)、程鄉(今廣東梅縣)的清軍吳六奇部,甚至南面的大海也不省心,時刻得提防著鄭成功這個“武裝乞丐”來“化緣”。
李定國當然想夾擊廣州,但郝尚久明顯拿不出手,唯壹靠譜的同盟,是活動在福建沿海的鄭成功。
如果鄭成功能率水師到廣東參戰,這盤棋顯然就走活了。尚可喜、耿繼茂根本就不是兩路大軍的對手,拿下廣州不過是時間問題。
奪取廣州,孫可望占據的雲南、貴州便可通過李定國控制的兩廣,與鄭成功、魯監國活動的福建、舟山連成壹片,形成西南、華南、東南“三南並舉”的局面。
夢想鼓舞人心,現實卻令人扼腕。——李定國謀劃得很到位,但鄭成功似乎對廣東興趣不大。
鄭成功到底怎麽想的,李定國並不清楚,但肇慶就在眼前,不打壹打,實在對不起如坐針氈的尚可喜。
三月二十六日,李定國大軍開始攻城,清總兵許而顯據城固守,雙方展開攻防激戰。
肇慶的許而顯比辰州的徐勇還要難對付,他不僅兵力較強,而且鬼主意多。看到南明軍架梯攀城,許而顯暗中派精兵出城迎戰,主要的任務是搶奪南明軍的雲梯。
梯子被“收繳”,李定國另出妙計——“上天”不行,咱就“入地”。於是,數萬南明軍成了“工程兵”,除了少數警衛以外,全都忙活著壹件事——挖地道。
雖然李定國在“工地”四周都拉上了帷幕,但城墻上的許而顯站得高看得遠,很快就發現了南明軍的新戰術。許而顯見招拆招,也開始在城墻內挖攔阻溝。
許而顯的“工程”有城墻擋著,李定國看不見,繼續搞自己的“人防工程”。兩支“施工隊”在肇慶幹得不亦樂乎,廣州的尚可喜卻坐不住了。他不知道許而顯能撐多久,更不知道自己能否撐得住。孔有德、尼堪都成了“戰神”李定國的刀下之鬼,尚可喜不希望成為第三個。
心虛膽寒的尚可喜壹面向清廷請援,壹面親自帶著援軍前往肇慶。耿繼茂沒跟著來,而是在三水設防,阻擊李定國派出聯絡郝尚久的部隊,謹防兵力空虛的廣州遭到偷襲。
尚可喜抵達肇慶後,於四月初八命大軍殺出城去,迅速擊潰李定國的警衛部隊,占領各地道口,接著以煙熏的方式消滅地道內的南明軍。此時,李定國的“施工隊”還在地道裏專心作業,出又出不來,有力沒處使,很多都被熏成了“臘肉”。
李定國被迫率部撤退,距離肇慶五裏下營,尚可喜乘勝追擊,壹舉沖破南明軍的臨時阻擊陣地,大獲全勝。南明軍敗局已定,李定國見奪取肇慶已成泡影,只能撤回廣西,整軍再戰。
大軍壹撤,郝尚久就慘了。
五月,駐防南京(清廷更名為江寧)的昂邦章京哈哈木、梅勒章京噶來道噶奉命率軍增援廣東。
援軍顯然來晚了,肇慶戰役早已結束。
總不能白跑壹趟吧?李定國撤回廣西,哈哈木的“牛刀”只能用來“殺雞”了。八月十三日,耿繼茂、哈哈木會同南贛的孔國治包圍潮州,郝尚久恐怕難逃此劫。
其實,早在李定國肇慶兵敗時,郝尚久就預感到形勢不妙,病急亂投醫,趕緊向“老冤家”鄭成功請援。鄭成功倒是很積極,於六月應邀而至。
但是,老鄭“三招不離本行”,他不是來幫忙,而是來“征糧”的。——餓死鬼投胎,沒辦法。
八月,鄭成功的“援軍”滿載糧食返回福建,郝尚久被徹底拋棄了。九月十四日,潮州失守,郝尚久自殺。
“戰神”再戰廣東
第壹次進軍廣東失利後,李定國認真總結了經驗教訓,並積極籌備第二次進軍廣東。
毫不誇張地說,這是南明實現“翻盤”的最佳時機!
其壹,前面說過,廣東是永歷政權實現“三南並舉”的最關鍵壹環。
其二,常年從事海外貿易的廣東經濟發達,稅賦是廣西的十倍以上,可以為抗清提供更加雄厚的經濟保障。
其三,也是最重要的,從雙方的態勢來看,廣東雖然不至於唾手可得,但也並非難事。
我們先分析壹下清、南明雙方的力量對比情況。
——清軍方面。
哈哈木、噶來道噶畢竟是來幫忙的,剿滅郝尚久之後,十月份便離開廣東。尚可喜、耿繼茂有多少人呢?兩萬?妳以為他們帶的都是“不死鳥”啊?
現實的情況是,尚可喜、耿繼茂的老部隊加起來還剩下不足五千人。盡管在當地有所補充,勉強招募到兩萬多人,但大部分“皆遊蕩之輩,俱非經戰之輩”。換句話說,不是老油條子,便是新兵蛋子。
——南明方面。
李定國入湘時的十萬大軍還剩下四萬多人(有些部隊沒有從湖南跟隨李定國到廣西發展,另有壹些戰鬥減員),很多都是大西軍時期的“老革命”,經驗豐富,英勇善戰。
鄭成功更猛,這些年在福建沿海“悶聲不響發大財”,兵力達到十萬以上,戰船上千艘,水師實力絕對是全國第壹。難怪他總是找郝尚久“打秋風”,海上又不能種地,靠著金門、廈門壹隅之地,養活這麽多人,實在是餓啊!
除了這兩只正規武裝以外,廣東各地的義師相當活躍。欽州、廉州有鄧耀等部,高州有周金湯,陽江沿海有李常榮,恩平有王興,臺山沿海有陳奇策。這些義師的前身大多是永歷政權的正規軍,普遍接受大學士郭之奇、南明兩廣總督連城璧的指揮。雖然實力有限,但由於地皮熟、人脈廣,作為“民兵”協助主力作戰還是綽綽有余的。
如此看來,真是天賜良機!
套用壹個英語句式:這個機會如此絕妙天成,以至於只會逃跑的朱由榔都看出來了!
永歷七年(1653年)九月,朱由榔派兵部職方司員外郎程邦俊趕赴廣東,向節制各地義師的郭之奇、連城璧宣諭,闡明“藩臣定國,戮力效忠,誓復舊疆”,嚴令郭之奇、連城璧務必聯絡廣東義師做好接應。
李定國派人聯絡鄭成功之後,於永歷八年(1654年)二月從柳州出發,經橫州、靈山進抵廉州,清總兵郭虎棄城而逃。南明軍相繼占領高州、雷州,廣東西部順利光復。
尚可喜、耿繼茂驚慌失措,壹面向清廷求援,壹面收縮兵力在廣州布防。廣東清軍並不經打,遠水又解不了近渴,如果不出意外的話,第二個孔有德即將在廣東誕生。
悲催的是,意外的事情再次“意外”地發生。四月,李定國患病,壹直到八月才基本痊愈。在此期間,既定的作戰計劃受到壹定影響。
不過,輕傷不下火線,重傷不進醫院的“戰神”李定國身體有恙,腦子卻不殘,依然在堅持指揮。
真正致命的意外,是鄭成功似乎“腦殘”了,居然沒動靜!
六月,稍事停頓的李定國大軍繼續向前推進,意圖奪取與鄭成功約定的會師地點——新會。同時,李定國再次派人前往廈門,催促鄭成功趕緊出兵參戰。
六月二十九日,新會戰役爆發。由於李定國身患重病,不能親臨壹線指揮,南明軍的作戰士氣受到很大影響。另外,南明軍缺乏水師助戰,打起來相當被動。壹個月過去了,近在咫尺的新會依然紋絲不動。
八月,李定國終於盼來了廈門的消息,但卻不是好消息。鄭成功使者姍姍來遲,言辭閃爍,李定國明白,援軍是徹底沒指望了。
鄭成功兩次“爽約”,看起來令人匪夷所思,其實理由很簡單。
其壹,鄭成功壹心要做福建的“土霸王”,不想插手廣東、幫別人打架,損耗自己的實力。
其二,鄭成功正在假意與清廷“和談”,趁機解決糧食問題。在這種情況下,他不想貿然出兵,打亂向清軍“征糧”的原定部署。
李定國缺乏後援,局面越來越被動。盡管陳奇策率舟師於八月參戰,控制廣州出海口,切斷了廣州與新會的聯系,但義師實力有限,南明軍的形勢依然在繼續惡化。
新會牽制著李定國的大軍,鄭成功又按兵不動,尚可喜、耿繼茂可以放心大膽地待在廣州固守待援。
十月初三,病愈的李定國親率大軍向新會發起新壹輪猛攻,地道戰、炮戰都用遍了,新會守軍依然負隅頑抗。
新會確實是塊難啃的硬骨頭,但城中的守軍日子也不好過。
由於被圍困了幾個月,城中的糧食已經消耗殆盡,餓著肚子的守軍開始向百姓伸手,“搜粟民家,子女玉帛,恣其卷掠”。到了十二月,百姓也斷了炊,從“掘鼠羅雀”到“食及浮萍草履”,將能吃的、不能吃的全吃了個遍,就差抱著城墻啃了,實在是慘不忍睹。令人發指的是,喪失人性的清軍無糧可掠,竟然戕殺居民為食!(兵又略人為脯臘,殘骼委地,不啻萬余。)
十二月初十,朱馬喇率援軍抵達廣東,十四日會同尚可喜、耿繼茂向南明軍發起總攻。四天激戰後,李定國全線潰退,除了留下幾千人鎮守羅定外,大軍主力悉數撤回廣西,第二次進軍廣東以失敗告終。
次年正月,羅定守軍撤回廣西。二月,李定國在清軍的追擊下退往南寧,南明“三南並舉”的重大轉機化為泡影。
失去孫可望的支持和鄭成功的協同,閃耀在“戰神”李定國頭上的光環,也開始黯然失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