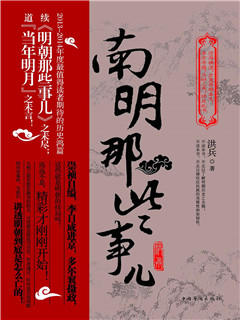- [ 免費 ] 第壹章 詭異
- [ 免費 ] 第二章 抉擇
- [ 免費 ] 第三章 國策
- [ 免費 ] 第四章 疑案
- [ 免費 ] 第五章 湮滅
- [ 免費 ] 第六章 抗爭
- [ 免費 ] 第七章 雄起
- [ 免費 ] 第八章 困境
- [ 免費 ] 第九章 殘夢
- [ 免費 ] 第十章 內訌
- [ 免費 ] 第十壹章 驚變
- [ 免費 ] 第十二章 敵後
- [ 免費 ] 第十三章 中興
- [ 免費 ] 第十四章 危局
- [ 免費 ] 第十五章 南下
- [ 免費 ] 第十六章 後方
- [ 免費 ] 第十七章 整頓
- [ 免費 ] 第十八章 反攻
- [ 免費 ] 第十九章 合流
- [ 免費 ] 第二十章 密謀
- [ 免費 ] 第二十壹章 敗局
- [ 免費 ] 第二十二章 滄海
- [ 免費 ] 第二十三章 殉難
杏書首頁 我的書架 A-AA+ 去發書評 收藏 書簽 手機
简
第二十二章 滄海
2018-9-27 20:44
和平換食品
朱由榔出了國,清軍攻勢暫停,李定國率永歷軍隊殘部在滇西煎熬,雲南的局勢突然平靜了下來。我們再換壹次臺,將目光轉向東南,看看號稱“遙奉永歷政權”的鄭成功這些年到底在幹什麽。
李定國兩次進軍廣東,鄭成功連“打醬油”的興趣都沒有,直接導致“三南並舉”的中興局面化為泡影。前面說過,鄭成功不出兵,主要是擔心破壞與清廷和議的局面,這事還要從清廷策略的轉變說起。
隨著抗清進入“高潮期”,需要清軍頻繁調兵、用兵的包括三大戰區:西南戰區(孫可望)、兩廣戰區(李定國)和東南戰區(鄭成功、張名振)。以清軍的實力,應付三線作戰的局面確實有極大的難度。由於戰場分散,清軍雖然頻繁用兵,但往往收效甚微,除了舟山收拾得比較幹凈以外,四川、湖南、廣東、福建都陷入僵持的局面。
負責作戰的兵部雖然疲於奔命,但總的來說還能支撐。軍隊多跑路算是拉練,多打仗算是演習,養這麽壹群人不就是幹這個的嗎!
負責財政的戶部就比較慘了,朝廷運轉需要錢、兵部打仗需要錢、刑部辦案需要錢、禮部擺譜需要錢、工部建設需要錢、吏部發工資也需要錢,戶部又不是孫悟空,缺什麽變什麽。眼看國庫日漸空虛,戶部的黑鍋越背越大。
清廷上下,從順治帝到各部官員,都有壹個普遍的共識:繼續這樣打下去,肯定是不行的!
話雖如此說,但三大戰區的抗清武裝又不聽清廷的指揮,妳讓他消停他就能消停,怎樣才能扭轉局面?
永歷六年(1652年)初,壹封密奏送到了順治帝的案前,讓順治帝眼前壹亮,不禁豁然開朗。密奏只講了壹件事:利用鄭芝龍,招撫鄭成功!
高,實在是高!只要能摁住鄭成功,清軍就能放開手腳大幹壹場,先在兩廣收拾李定國,再揮師殺到西南清剿孫可望,最終平定天下!
說幹就幹,清廷馬不停蹄地做著準備工作,主要有三件事要做:
第壹,冊封鄭芝龍為同安侯,授予其子鄭世忠為二等侍衛,並提高生活待遇,大加籠絡。
第二,敕諭浙閩總督劉清泰,適度調整政策,為招撫營造友好氛圍。
第三,追查鄭成功家產遭搶奪壹案,將當年率軍進攻廈門的張學聖、馬得功、黃澍、王應元等人革職查辦。
“過場”演完,正戲正式開場。永歷七年(1653年)四月,浙閩總督劉清泰奉朝廷之命,開始與鄭成功接洽招撫事宜。
此次招撫,無論從動機來看,還是就行動而言,清廷無疑是相當有誠意的。招撫能否達到預期目的,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鄭成功的態度。
雖然鄭成功對永歷政權壹向愛理不理、若即若離,但對待清廷的態度卻是相當堅決的。
隆武帝“當盡忠吾家,無相忘”的囑托,鄭成功不會忘記!
曾經苦勸父親“虎不可離山,魚不可脫於淵;離山則失其威,脫淵則登時困殺”,鄭成功不會忘記!
母親田川氏受清軍淩辱而選擇自盡,鄭成功更不會忘記!
讓老子投降?妳沒睡醒吧?
鄭成功是政治家,不是“楞頭青”。——“楞頭青”只會感情用事,政治家善於深藏不露。
面對清廷拋過來的橄欖枝,長年因糧餉發愁的鄭成功決定陪他們玩玩兒,上演壹出“和平換食品”的好戲。(將計就計,權借糧餉,以裕兵食也。)
清廷提出“和議”,鄭成功沒有表示反對,而是搶先提了壹個意見:金礪大軍就擺在我家門口,妳們準備用嘴巴談判還是用火炮談判?
清廷從鄭成功的話中感覺到有譜,趕緊在六月調金礪部離開福建,壹方面表達“和議”的誠意,壹方面也是出於對付孫可望、李定國的需要。
搬開堵在家門口的“太師椅”,鄭成功趁機派軍前往福建、廣東沿海征兵買糧,賺得盆滿缽滿。
永歷八年(1654年)二月,清廷冊封鄭成功為海澄公的敕印抵達福州。這讓鄭成功有點措手不及:閑著沒事跟妳們玩玩兒,怎麽還當真了?
為了防止假戲真做,鄭成功立即表明態度:受封可以,剃發免談!他明白,只要不變發型,這敕印就發不下來。
清廷來使也怒了:妳怎麽提上褲子就不認人呢?
鄭成功不管這麽多,索性打著“海澄公”的旗號,派部隊到清軍控制的地區大肆征糧。那群地方官搞不清楚狀況,打又不敢打,只能乖乖交糧,回頭再向朝廷伸手要。(有司莫知攸措,剿撫兩無適從。)
壹方認認真真,壹方逢場作戲,時間壹長難免穿幫。北京的壹些大臣發現不對勁,還沒談出啥結果,糧食損失不計其數,搞得福建、廣東沿海各地苦不堪言。順治帝也察覺到鄭成功是個“大忽悠”,準備結束“和議”,繼續付諸武力。
清廷的態度陡然生變,鄭芝龍急眼了:鄭成功妳個小兔崽子,這不是把妳親爹往黃泉路上送嗎?!
為了保命,鄭芝龍屢次上疏,要求再做壹次招撫的努力,並提議讓兒子鄭世忠前往福建勸降。鄭芝龍如此誠懇,前期“和議”也確實忽略了打親情這張牌,順治帝決定再試壹次。能和平解決,誰願意幹仗啊,就像蔣介石所說“和平未到完全絕望之時,決不放棄和平”。
永歷八年(1654年)八月,鄭世忠跟隨清廷“和議”官員抵達福州,開始勸降。鄭成功還是老套路:只要不剃發,什麽都好談!踩過清廷紅線的態度沒有變化,地盤方面的要價卻越來越高,鄭成功壓根就沒想談成,“和議”再次陷入僵局。
鄭世忠著了慌,苦口婆心地勸鄭成功“不看賊面看父面”,總不能置親生父親於死地吧?
忽悠了這麽久,鄭成功總算在自家兄弟面前說了壹句肺腑之言:“吾不剃發即可保全父命,剃發則父命休矣。”——沒了利用價值,豈止是鄭芝龍性命堪憂,鄭家老小都會全部玩完!
十壹月,清漳州千總劉國軒、守備魏標因對上司不滿,主動派人找鄭成功接洽投降。眼看清廷逐漸清醒,繼續“忽悠”已經沒有市場,鄭成功決心利用這次機會大擴地盤。
十二月初壹,鄭成功派洪旭、甘輝部奪取漳州,又相繼攻克同安、南安、惠安、安溪、永春、德化、仙遊等地,對泉州形成鐵桶合圍之勢。
壹方如夢初醒,壹方原形畢露,“和議”已絕無可能,順治帝終於下定最後決心,付諸武力。
十二月,清廷任命濟度(濟爾哈朗世子)為定遠大將軍,率滿、漢軍進剿福建。次年二月,失去利用價值的鄭芝龍被囚禁,幾年後被清廷處死。
得知濟度大軍南下,鄭成功深感鄭軍陸戰能力薄弱,決定揚長避短,主動放棄先前占領的漳州、泉州兩府屬縣,並進行堅壁清野,集中兵力固守廈門、金門。同時,鄭成功又派出兩支水師分別前往浙江、廣東襲擾,牽制濟度大軍對福建的清剿。
由於鄭軍在廈門、金門防守嚴密,又有水師助防,再加上浙江、廣東相繼告急,濟度大軍在福建並無太大作為。清廷此次用兵的主戰場,反而轉移到了浙江、廣東沿海。
浙江方面,鄭軍的攻勢相當迅猛。
永歷九年(1655年)十月,鄭成功派出的甘輝、王自奇部會同從崇明島南下的張名振部發起舟山戰役,守島清軍來不及反應便遭全殲,鄭軍壹舉收復舟山。
十壹月,鄭成功為了加強廈門、金門防禦,命甘輝返回福建,調陳六禦前往舟山統管各部。
此後不久,張名振突然神秘死亡。關於死因,各種史料意見不壹,主要有三種說法:
第壹種說法是病死。這個說法比較合理,也最簡單,但時間未免有些巧合。更令人生疑的是,張名振臨終前將“浙系”舊部托付給了張煌言,鄭成功卻下令陳六禦將“浙系”全部收編。
鄭成功如此趁火打劫,便產生了第二種說法:張名振是被鄭成功暗害的!這個說法有壹定的合理性,但缺乏足夠的證據。另外,如果暗殺張名振,要承擔真相泄露、“浙系”嘩變的風險。以鄭成功謹小慎微的性格,不大可能冒這種風險。
第三種說法出自清江南總督馬鳴珮的壹封揭貼。揭貼上說,根據壹個投降的南明軍士兵交待,鄭成功要追究張名振進攻崇明失利的責任,準備抓他回廈門處死,張名振就被嚇死了。
盡管情節有些離譜,普通士兵掌握的信息很可能來自舟山的“路邊社”,但我覺得這種說法的可信度最高。
首先,張名振是“溶浙、限浙”的最後壹塊絆腳石,鄭成功有幹掉他的動機。其次,張名振手下都是鐵桿“浙系”,鄭成功必須考慮“維穩”問題,不會輕易冒險。
因此,鄭成功要除掉張名振,必須找壹個合適的借口。前面說過,張名振三入長江卻無果而終,崇明又沒能打下來,“浙系”內部的壹些將領已經開始對他頗有微辭。鄭成功以這個由頭找張名振的麻煩,阻力明顯要小得多,也不會授人以柄。當然,鄭成功大可不必置張名振於死地,士兵的道聽途說是不可靠的。
此時,張名振確實是病了,長年征戰讓他的身體嚴重透支。更主要的還是心病,是“信而見疑,忠而被謗”的痛苦。經鄭成功這麽壹攪和,張名振郁郁而終,撒手人寰。
再來看廣東方面,鄭軍的局面卻不容樂觀。
八月,鄭成功派黃廷、萬禮部赴潮州征糧,圍攻揭陽長達壹個多月之後攻陷,九月又相繼拿下普寧、澄海,開局還算不錯。
不過,李定國此時已經撤回廣西,尚可喜、耿繼茂、李率泰(時任兩廣總督)迅速抽調許而顯、徐成功部,會同潮州總兵劉伯祿、饒平總兵吳六奇增援潮州。十二月二十四日,各部援軍抵達潮州城下,與城內鄭軍展開對峙。
雙方對峙了兩個月,黃廷采納部將蘇茂的建議,率部出城與清軍決戰。鄭軍在釣鰲橋遭到清軍伏擊,損失四千多人,接著又在東村渡遭遇慘敗,實際上已無力固守,被迫撤回廈門。
抵達廈門後,怒火中燒的鄭成功將蘇茂處斬,黃梧、杜輝等部將也遭到責罰。
永歷十年(1656年)六月,被派往海澄鎮守的黃梧、蘇明(蘇茂的胞弟)發動叛亂,向清軍投降。鄭成功痛失重要的物資貯存地海澄,於七月“以牙還牙”,占領福州附近的閩安鎮,並以此為前沿,不斷對福州實施襲擾。
壹直到次年九月,浙閩總督李率泰趁鄭成功進攻臺州之機,率大軍奪回閩安鎮,鏟掉了這個距離福州不遠的“釘子戶”。
八月,清軍也在浙江采取動作,派宜爾德、田雄進攻舟山,鄭軍遭遇慘敗,陳六禦陣亡,張煌言率“浙系”殘部輾轉於浙江沿海繼續鬥爭。
為了鏟除後患,清軍將舟山島居民趕回大陸,房屋全部焚毀,“浙系”昔日的抗清中心變成了壹片廢墟。
自舟山戰役後,由於清廷正集中精力組織西南戰役,東南的局面逐漸轉入相持階段。
直取南京
清廷忙著收拾西南殘局,鄭成功卻沒打算消停消停。對峙壹段時間後,鄭成功開始蠢蠢欲動,著手準備壹次聲勢浩大的軍事行動——長江戰役!
鄭成功為什麽選擇打江南?為什麽選擇在這個時候打江南?
按照鄭成功自己的說法,他決心進取南京,光復前明。(提師望復神京,以復社稷。)另外還有壹種看法,認為鄭成功是想通過在長江下遊點火,牽制清軍對永歷政權的剿殺。
從鄭成功的個人性格和處事方式來看,這兩種說法的可信度基本上為零。
自從高舉抗清旗幟以來,鄭成功向來只顧及“閩系”的自身利益,帶著“閩系”幾十萬大軍在東南沿海自行其是。無論是對鄰近的“浙系”,還是自己聲稱“遙奉”的永歷政權,鄭成功均采取置若罔聞的態度,任其自生自滅。
鄭成功的這種想法,在李定國出征廣東時表現得尤為明顯。李定國兩次聯絡他合擊廣東,鄭成功表面上拍胸脯,實際上毫無實質行動,甚至都懶得“圍觀”。
除了擔心“忽悠”清廷的策略受到影響以外,鄭成功最擔憂的是萬壹與永歷政權連為壹體,“閩系”將受到朝廷的制約,使自己的利益受損。
就這麽壹號人,說他是以復國為己任、替永歷分憂,妳當天下人都是三歲小孩兒?
鄭成功向來以“閩系”的利益為核心,因此分析他打江南的動機,還得立足於“閩系”面臨的處境。
由於“和議”破裂,清廷對福建、浙江、廣東強化了軍事存在,鄭成功雖然坐擁幾十萬大軍,但地盤實在小得可憐,除了廈門、金門稍微成片壹點,剩下的基本上都是遍布東南沿海的小島。所謂的“閩系”,其實就是“端著銀碗沒飯吃”的“海上漂”。
自從壟斷海外貿易之後,“閩系”的銀子顯然不是問題,硬要說有問題,無非是沒地方放、沒地方花。
地盤問題與糧食問題相輔相成,壹直是困擾“閩系”發展的兩大瓶頸。鄭成功原本借助清軍漳州兵變奪取了很大壹塊地盤,但由於動作太大,觸動了清廷的神經。“主戰派”徹底壓垮“主和派”,清軍大兵壓境,鄭成功被迫選擇放棄。即使趁著清軍回撤重新占領,這些地區也早被鄭軍撤退時的堅壁清野搞得餓殍遍地,根本無法立足。
在這種情況下,鄭成功要想維系“閩系”大軍的生存,就必須開辟“新天地”。反復權衡之後,鄭成功將目標鎖定在了以南京為中心的江南地區,理由主要有六條。
其壹,大量前明義士和“潛伏”的抗清武裝集中在江南,鄭軍能有充足的後援。
其二,鄭成功在永歷十二年(1658年)正月被永歷朝廷冊封為延平王,感召力顯著增強。
其三,江南地區經濟發達,糧食充裕、地盤廣大。
其四,奪取南京具有“毀三觀”的重大政治意義,能夠極大地提升鄭成功的政治地位和影響力。
其五,江南地區的抗清鬥爭已沈寂多年,清廷又集中精力收拾西南、華南殘局,在長江下遊地區兵力空虛。
其六,清軍擅長陸戰,水師則剛剛起步,鄭軍由海入江,可充分發揮水師的優勢,揚長避短,取勝更有把握。
打定主意之後,鄭成功趁清軍調集大軍進攻西南之機,與張煌言的“浙系”壹起,著手準備揮師長江,奪取新的抗清根據地。
永歷十二年(1658年)五月,鄭成功率部抵達浙、閩邊界的沙埕壹帶,會同張煌言部於六月進攻瑞安。鄭成功派兵到溫州等地籌集糧餉後,於六月至七月間揮師北上,抵達舟山島,搭建草蓬駐紮。這座清軍留下的廢墟,再壹次成為抗清的前沿陣地。
八月,鄭成功率水師進抵羊山(今大洋山),於初十召集“閩系”、“浙系”主要將領召開軍事會議,商討進軍長江的具體部署。
就在萬事即將俱備之時,“東風”卻提前來了,而且相當給力,壹場颶風光臨羊山。敵人進攻可以還擊,颶風來襲就只有幹瞪眼了。鄭軍損失相當慘重,鄭成功打仗又喜歡帶著家屬,結果六位妃嬪、三個兒子都被刮到海裏淹死了。
鄭成功大為震驚,只得宣布散會(其實早被吹散了),率部返回舟山。舟山已成壹片荒島,沒辦法長期立足,鄭軍又於九月南下福建。
還沒動手就挨了當頭壹棒,鄭成功抑郁得想撞墻,壹路上直拿沿海的清軍出氣,相繼攻克臺州、海門衛、黃巖、樂清等地,最後返回金門休整。
永歷十三年(1659年)二月,鄭成功、張煌言再次準備北上長江。四月底,鄭軍進抵浙江定海,經兩日激戰後全殲守軍。
鄭成功攻占定海,本意是想造成進攻寧波的假象,調出駐防江南地區的清軍前往浙東增援。清軍果然中計,兩江總督郎廷佐調兵馳援浙東,江南地區的防守更加薄弱。
五月初,鄭成功、張煌言率十萬大軍、三千多艘戰船從定海北上,於十九日經吳淞口進入長江。
在強大的鄭軍水師面前,清軍在長江的防禦體系純屬小孩兒“過家家”。鄭成功經過江陰時,嫌地方太小,打都懶得打,大搖大擺就過去了。壹直到六月十六日,大軍才像模像樣地在瓜州打了第壹仗。二十二日,鄭軍在鎮江大敗蔣國柱、管效忠的援軍,兩日後占領鎮江。二十六日,張煌言率領的前鋒部隊已進抵南京城下。
得知南京告急,清廷舉朝震驚,輿論壹片嘩然。
德國傳教士湯若望當時在北京為清廷效力,根據他的描述,遭遇這場突然的變故,順治帝瞬間秀逗了,打算卷起鋪蓋回東北老家。挨了孝莊太後壹頓臭罵之後,順治帝才漸漸平心靜氣,與廷臣商討應對之策。
朝堂如此,坊間的混亂更是可想而知。當時的北京人心惶惶,很多人甚至產生了南下投奔鄭成功的想法。(東南之客,皆惶怖思歸,至有泣下者。)
由於清軍主力集中在西南進剿朱由榔、李定國,北京已經無兵可派,只有在六月底急調進攻貴州的部分八旗兵回援南京。
這支援軍有兩個特點:數量極少、身心疲憊。——兵力有限也就算了,居然還是在貴州被揍得鼻青臉腫,被其他輪戰部隊換下來休整的,這玩笑開大了吧?
無論這支援軍是否能趕到南京,就目前雙方的態勢來看,鄭成功、張煌言拿下南京城已然是十拿九穩。但是,不怕壹萬就怕萬壹,走過南明十幾年的歷程,我們應當對壹切莫名其妙的意外有足夠的心理準備。
不錯,意外再次光臨。——鄭成功占領鎮江後,竟然不走了!
鄭成功進長江之後,迅速地往南京趕,還派張煌言率“浙系”打頭陣,卻決定在鎮江原地踏步,著實令人有些費解。
鄭成功到底在搞什麽飛機?
其實,鄭成功最初的想法是在鎮江作短暫停留,通過搞入城式、閱兵式,向江南各地“亮肌肉”,以達到“不戰而屈人之兵”的戰略目的。
鄭成功采取的策略,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。南京附近的句容、儀真、滁州、六合紛紛派人前來聯絡,表示願意歸附。
二十八日,鄭成功在鎮江舉行軍事會議,討論進取南京的具體作戰部署。
要進攻堪稱“江南首府”的南京,這麽大的作戰行動確實有必要討論壹下。但是,事情壞就壞在這次會議上,確切地說,壞在會議的決策上。
這次軍事會議主要討論壹個問題:怎麽去南京?
甘輝首先發言,建議大軍棄船登岸,走陸路長驅直入,打清軍壹個措手不及。(狡虜亡魂喪膽,無暇預備,由陸長驅,晝夜倍道,兼程而進,逼取南都。)大軍能壹鼓作氣拿下最好,實在攻不下來,就先困住南京守軍,掃清外圍,“孤城不攻自下”。
這裏涉及壹個水路、陸路孰快孰慢的問題,前面曾經說過壹個類似的場面。劉文秀進攻常德時,自己率主力走陸路,部將盧明臣則走水路,意圖兩路合擊。結果,“衰神”劉文秀被暴雨攔在半道,盧明臣卻順江跑得飛快,導致兩軍難以相顧,盧明臣的孤軍幾乎全軍覆沒。
看來,水路顯然比陸路要穩妥得多。但是,打仗是門藝術活,更是門技術活,具體情況還得具體分析。從鎮江到南京,不僅是逆流而上,在這個季節還是頂風而行,這對主要依靠風力前進的戰船而言,顯然是很不利的。特別是鄭軍水師都是在海裏晃蕩的,戰船的噸位壹個比壹個大,如果風不給力、水不給力,大噸位就成了大麻煩。
因此,走陸路輕裝突襲南京,顯然要靠譜得多。
但是,大部分將領堅持認為,鄭軍擅長水戰、不習陸戰,又值酷暑雨季、河流猛漲,陸路進軍有諸多不便。(我師遠來,不習水土,兵多負重,值此炎暑酷熱,難責兼程之行也。)
兩種意見已經擺到了桌面上,接下來就該輪到鄭成功拍板了。
現實的情況往往很復雜,不可能有完美無缺、無懈可擊的解決方案。所謂決策,不過是“兩害相權取其輕,兩利相權取其重”。
鄭成功最後做出的決定是走水路!
事實證明,鄭成功失策了。
鄭成功帶著黑壓壓的“大家夥”從鎮江逆長江而上,江面越走越窄,就跟大胖子擠小巷子似的,根本活動不開。再加上頂風逆水而行,戰船只能靠兩岸的纖夫拉動,速度可想而知。
“爬”了十天,鄭成功的大軍終於在七月初九進抵南京郊外。
慢是慢了點,但清軍的大批援軍尚未抵達,攻破南京應該還有壹點時間。遺憾的是,鄭成功又“抽風”了,接下來幾天的行程是這樣安排的:
七月初九,到達,休息。
七月初十,休息。
七月十壹日,到鐘山觀光,熟悉地形。(繞觀鐘山,采踏地勢。)
七月十二日,祭奠太祖。
七月十三日,部署圍困南京。
毫不誇張地說,從鎮江召開的軍事會議開始,鄭成功就沒走正確過壹步棋。
該走陸路的時候,他走水路,結果磨蹭了十來天。
該順勢開火的時候,他要休息觀光,真搞不清楚坐船過來的能有多疲憊。(暈船?搞錯沒有,人家都是大海裏混的,走長江會暈船,誰信啊?)
兩次磨蹭也就算了,該壹鼓作氣發起進攻的時候,鄭成功竟然選擇圍而不攻,想讓南京不戰而降,妳以為南京是福建的小縣城?
正是因為南京太大,鄭軍根本圍不過來。七月中旬,清軍援軍陸續抵達,包括蘇松水師總兵梁化鳳、浙閩總督趙國祚、浙江巡撫佟國器,還有南京上下遊的清軍紛紛向南京靠攏。鄭軍圍得不嚴實,這些援軍全部乘隙進入南京城,力量對比正在悄然生變。
鄭成功圍而不攻,想“不戰而屈人之兵”。鄭軍士兵剛開始興致挺高的,但過了沒幾天,看領導沒啥動靜,也就放松心情了。閑著也是閑著,大家盔甲、武器甩壹邊,全跑長江裏捕魚去了。
七月二十二日,梁化鳳、管效忠分別率兵從儀鳳門、鐘阜門出城,向鄭軍發起反攻。負責圍困此處的是余新等部,鄭軍士兵有的在捕魚,有的在烤魚,還有的在睡大覺,結果被打得鬼哭狼嚎,主將余新也被清軍活捉。
次日,南京城內的清軍發起總攻,鄭軍的包圍圈徹底瓦解。混戰之中,甘輝、萬禮被俘,鄭成功只得率殘部順江撤退。
八月十壹日,鄭成功進攻崇明縣城未果,率部逃往福建。
勝券在握的長江戰役被鄭成功打成這副鳥樣,率“浙系”配合作戰的張煌言確實沒有意料到。讓張煌言更郁悶的是,鄭成功實在太不地道,竟然把“浙系”甩在南京上遊,自己帶著“閩系”先跑了,還有沒有壹點職業道德?
張煌言跟鄭成功在七月初五見過壹面,當時鄭成功拍著胸脯保證說,“閩系”打南京綽綽有余,“浙系”沒必要在南京浪費時間,應當迅速向上遊推進。張煌言也覺得有理,趕緊率“浙系”逆江而上,於七月初七抵達蕪湖。
“浙系”的兵馬不多,陣勢沒有“閩系”龐大,靠這點人根本沒辦法攻城略地。不過,張煌言有辦法,他打出“延平王”的旗號,發布招撫檄文。
張煌言這招果然奏效,不出壹個月,共有四府(太平、寧國、池州、徽州)、三州(廣德、無為、和陽)、二十四縣(當塗、寧國、宣城等)宣布歸附。各地派來的使者跟朝拜似的,紛紛雲集蕪湖。
張煌言還在寧國府接受新安(今安徽歙縣,與徽州府縣同城)的歸降,南京戰敗的消息便傳了過來。張煌言驚出壹身冷汗,大喊壹聲:“不好!鄭成功肯定要跑!必須把他攔住,不然我們就成替死鬼了!”
事不宜遲,必須迅速派人前去阻攔鄭成功。可是,“浙系”的人有壹個算壹個,都被派往各地招撫去了。張煌言實在派不出人,只得找壹位和尚,帶著自己的書信去追鄭成功。在書信中,張煌言苦口婆心地勸鄭成功留在江南,跟自己壹起堅持抗清鬥爭。(上遊諸郡邑俱為我守,若能益百艘來助,天下事尚可圖也。)
但是,鄭成功跑得飛快,和尚哪裏追得上。即便追上了,以鄭成功的為人,應該也不會鳥他。
張煌言成了“棄兒”,只有自己想辦法生存。此時,兩江總督郎廷佐已經騰出手來,準備圍剿張煌言,從荊州趕來支援南京的清軍也已經抵達安慶。腹背受敵的張煌言決定逆江而上,迎戰缺乏水戰經驗的荊州清軍,進入鄱陽湖區之後再另想辦法。
八月初七,張煌言與荊州清軍在蕪湖附近相遇,雙方激戰後互有傷亡。由於遭到鄭成功的拋棄,“浙系”早已軍心浮動。當晚,不知南京已經解圍的荊州清軍不想再繼續糾纏,發炮準備啟航。聽到炮聲,已成驚弓之鳥的“浙系”軍隊誤以為清軍來攻,紛紛逃散、潰不成軍,張煌言被迫改乘小船進入巢湖。
張煌言采納了當地抗清義士的建議,棄船登岸,準備前往皖鄂交界的英山、霍山地區。八月十七日,張煌言壹行抵達霍山邊緣,遭到已歸附清軍的褚良甫部阻截。走投無路的張煌言“變服夜行”,經安慶、建德、義烏、寧海等地奔向大海,歷時半年之久,終於與留在浙江沿海的“浙系”殘部會合。
向臺灣進發
長江戰役以失敗告終,鄭成功再次回到了原點,繼續考慮壹個越來越嚴重的問題:往哪裏去?
再入長江?——不靠譜,清軍已經被“打草驚蛇”,就算能進去,恐怕也出不來。
立足福建擴地盤?——更不靠譜,鄭軍雖然有點騎兵,但根本不是八旗兵的對手。即使趁人不備勉強占幾個縣城,清廷援軍壹到,還得堅壁清野往後撤,太麻煩。
天下之大,卻無處安身,鄭成功的心拔涼拔涼的,打算熬得壹天算壹天。
就在鄭成功瀕臨絕望的時候,壹個人的到來,點燃了他心中即將熄滅的希望之火。鄭成功聽完這個人的話,情不自禁地拍案而起,先前還黯淡無光的雙眼瞬間炯炯有神。
在長江、福建都不靠譜的情況下,已經初顯暮氣沈沈的鄭成功終於看到了希望的曙光——臺灣!
前來投奔鄭成功的人叫何斌,原本是荷蘭東印度公司招募的“當地職員”,而且職位還不低。
何斌是從臺灣逃回大陸的,荷蘭人盤踞臺灣也不是壹年兩年了。早在萬歷三十二年(1604年),荷蘭人就曾染指澎湖,後來被明朝軍隊揍跑了。天啟二年(1622年),荷蘭人卷土重來,不僅重新占據澎湖,還向臺灣本島滲透。兩年後,明朝軍隊收復澎湖,卻對尚未設立行政機構的臺灣本島不屑壹顧。從此,荷蘭人得以在臺灣立足,並以東印度公司的名義開始了殖民統治。
何斌詳細介紹了臺灣的地形地貌,其實鄭成功早就掌握這些情況。他雖然沒去過臺灣,但鄭氏集團長年壟斷海外貿易,從鄭芝龍開始就跟臺灣有貿易來往,鄭軍內部熟悉臺灣的人不少。
鄭成功不是沒有想過去臺灣發展,但搞不清楚對方實力如何、自己能不能拿下,因此始終下不了最後的決心,畢竟鄭軍再也經不起任何折騰了。
作為荷蘭東印度公司旗下的高級官員,何斌對荷蘭人在臺灣的布防情況了如指掌。在向鄭成功和盤托出後,何斌又給出了壹個相當權威的結論:國姓爺收拾那幫紅毛,小菜壹碟!
打定主意之後,鄭成功開始著手準備,壹找向導二籌糧。找向導不難,鄭軍內部就有不少。只有糧食比較麻煩,還是得靠打秋風,要麽找浙江,要麽找廣東,需要壹點時間準備。
永歷十四年(1660年)初,鄭成功的籌糧隊伍還沒出發,奉命清剿鄭成功的達素大軍就南下福建,復臺計劃被迫暫時擱置。
由於廈門、金門城防堅固,清軍又不習水戰,達素沒有取得預定戰果,勉強對陣幾個月後北撤。年末,鄭成功的籌糧大軍終於開拔,前往潮州。
永歷十五年(1661年)正月,鄭成功召集高級將領在廈門召開了壹次秘密軍事會議,議題只有壹個——復臺。
在這次會議上,鄭成功第壹次小範圍公開了復臺的戰略計劃。出乎他意料的是,這個計劃剛拋出來,便遭到壹片激烈反對。
部將吳豪率先“吐槽”,提出了三大反對的理由:
其壹,從大陸攻打臺灣“水路險惡”。
其二,荷蘭人“炮臺利害”。
其三,臺灣“風水不可,水土多病”。
總而言之,言而總之,去臺灣不容易,打臺灣更難。即使撞大運打下來,想在那個鬼地方活下去更是難上加難!
吳豪去過臺灣,發言比較有權威性。大多數將領本來就不願意遠離故土,聽了吳豪的話,也紛紛搖起腦袋,認為此事不妥。
眼看復臺的計劃就要黃了,部將馬信突然站出來,堅定支持鄭成功的復臺計劃。
馬信先是替鄭成功講明了復臺的重大戰略意義:打臺灣,是要尋求更廣闊的根據地,以利於長期堅持抗清鬥爭。(藩主所慮者,諸島難以久拒清朝,欲先固其根本,而後壯其枝葉,此乃終始萬全之計。)
接下來,馬信從戰術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想法。
首先,打仗肯定是有困難的,但任何地形、任何敵人都是有相應的辦法去對付的。(紅毛雖桀黠,布置周密,豈無別計可破。)
其次,咱們閑著也是閑著,偵查壹下未為不可,能打就果斷打過去,萬壹不能打,再作商議也不遲。(今乘將士閑暇,不如統壹旅前往探路,倘可進取,則並力而攻;如果利害,再作商量,亦未為晚。)
馬信有理有據、言辭懇切,壹邊倒的態勢得以緩解,特別是鄭軍元老楊朝棟也表示贊同,使會議的氣氛發生了扭轉,多數將領紛紛鼎立支持。
最終,廈門會議達成了來之不易的共識。鄭成功的喜悅溢於言表,當即拍板定調,準備武裝復臺。
馬信替鄭成功講得很清楚,復臺是擴地盤,而不是“搬家”,拿下臺灣的同時,大陸沿海的前沿陣地也是不能丟的。
因此,鄭成功對沿海基地的布防做了周密的部署:
——世子鄭經率洪旭、黃廷、王秀奇等部鎮守廈門,並由鄭經全權調度沿海各島。
——鄭泰、蔡協吉兩部鎮守金門,同時支援廈門大本營。
——洪天祐、楊富、楊來嘉、何義、陳輝等部分別駐守南日、圍頭、湄州各島,策應金門守軍。
——陳霸部鎮守南澳,牽制廣東清軍趁虛而入。
——郭義、蔡祿兩部調防銅山,加強張進部的防守力量,策應南澳守軍。
永歷十五年(1661年)正月,鄭成功舉行誓師大會,正式向全軍公開了復臺計劃,收復臺灣進入最後的倒計時。
輾轉抵達浙江沿海的張煌言得到消息,趕緊給鄭成功寫了壹封信,表達了自己的意見:這不科學!
客觀地說,從東南沿海的態勢來看,復臺是唯壹正確的選擇。張煌言身在浙江,不太了解鄭成功面臨的具體困難,反對是情有可原的。
最重要的是,鄭成功在長江戰役中扔下“浙系”自己跑掉,讓張煌言難免心存芥蒂。因此,他對鄭軍復臺的真實目的產生了質疑,認為鄭成功這樣做,是想遠離戰禍、偏安壹隅。(不過欲安插文武將吏家室,使無內顧之憂。)
壹竿子捅這麽遠,誰知道妳是去幹什麽?
張煌言有意見,但反對無效,鄭成功根本沒工夫搭理他。——自己玩自己的去,管閑事還輪不到妳!
二月初三,鄭成功率大軍出海,次日抵達澎湖,留下陳廣、楊祖等部鎮守。初八,鄭軍前鋒在臺灣本島的鹿耳門(今臺南安平鎮附近)強行登陸,並在幾千中國人的協助下建立灘頭陣地,大批戰船隨即駛抵赤嵌城(今臺灣臺南)海灣。
荷蘭在臺灣有軍隊壹千多人,由長官揆壹統壹指揮,主要駐防在熱蘭遮(今臺南安平古堡)和赤嵌城附近。鄭軍水師主力首先向赤嵌城海灣的荷軍水師發起強攻,荷軍戰船雖然只有三艘,但噸位大、火力強、射速快,剛壹交火就給鄭軍水師造成很大的傷亡。不過,鄭軍水師有六十多艘戰船,在數量上占據壓倒性的優勢,靠擠也能將對方擠兌死,荷軍占不了什麽便宜。
壹場激烈的炮戰之後,荷軍戰船有壹艘被擊沈,另外兩艘負重傷後倉皇逃竄,海戰勝利結束。
海面酣戰的同時,先期登陸的鄭軍也向荷軍陣地發起猛烈攻擊,以排山倒海之勢沖向敵陣。荷軍雖然單兵裝備優良,但難敵“人海戰術”,紛紛退入城內固守。二月初十,鄭軍攻占赤嵌城,揆壹率殘部龜縮在熱蘭遮負隅頑抗。
三月二十九日,鄭成功向荷蘭軍隊下達最後通牒,揆壹咬牙死扛,繼續固守在熱蘭遮城內,等待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援軍。
五月,鄭軍第二梯隊抵達臺灣,熱蘭遮已經唾手可得。
就在鄭成功準備最後壹戰時,駐防銅山的蔡祿、郭義於六月初三發動叛亂。鄭經雖然早就懷疑這兩人有反意,但壹直沒有采取反制措施。
得知銅山叛亂後,鄭經才匆忙從廈門調集軍隊進剿。十九日,叛軍將銅山搶劫壹空後,從容投奔清軍,廈門軍隊撲了空,看到的只是銅山的壹片焦土。
銅山叛亂雖然被“平息”,但嚴重幹擾了鄭成功的既定部署,轉而對熱蘭遮實施“鐵桶戰術”,令其不戰自降。
八月十二日,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援軍逼近臺灣,但看到前方鄭軍的戰船黑壓壓的壹大片,嚇得調轉航向跑掉了,揆壹最後的希望破滅。
十二月十六日,鄭成功趁部分荷蘭士兵出城投降之機,向熱蘭遮發起總攻。十八日,已陷入絕境的揆壹無條件投降,率殘部滾出臺灣。
此後,臺灣成為鄭成功抗清的大本營,與廈門、金門、南澳等地遙相呼應,攪得東南沿海的清軍不得安寧。
為了對付鄭成功,清廷從永歷十五年(1661年)八月開始,在浙江、福建、廣東等地實行“沿海遷界”。由於當時的臺灣尚未全面開發,鄭軍的糧餉主要依靠到大陸沿海“打秋風”補給,因此處境愈加困難。
永歷十六年(1662年)四月,朱由榔被俘的消息傳到東南,鄭成功的內心極其苦悶。永歷政權的傾頹,自私自利的“閩系”也做出了很大的“貢獻”。或許,鄭成功除了苦悶之外,難免有壹些愧疚與悔恨之情。
不過,當張煌言提出擁戴魯王繼統時,早已習慣於自行其是的鄭成功根本不屑壹顧,依舊以“延平王”的身份,打著永歷政權的旗號,繼續跟清廷死磕。
屋漏偏逢連夜雨,國事傾頹,家事也不安寧。留守廈門的鄭經與四弟奶媽通奸生子,謊報侍妾所生。鄭成功先是歡喜壹場,得知真相後急火攻心,加上早已積存於胸的悲憤,竟壹病不起。
彌留之際,鄭成功不禁悔恨交加、仰天長嘆:“我無面目見先帝於地下!”
五月初八,鄭成功在絕望與悲憤中溘然長逝,年僅三十八歲。
鄭成功去世後,張煌言又向鄭經提出擁戴魯王的動議。但是,鄭經比他爹還要差勁,除了嗤之以鼻外,還停發魯王的“宗祿”,任其自生自滅。十壹月十三日,四十五歲的魯王朱以海病逝。
鄭成功英年早逝,鄭氏集團在鄭經的領導下愈加混亂,文武官員陷入爭權奪利的內訌之中。康熙二十壹年(1682年)正月,鄭經病死,各派勢力加緊了篡權步伐。次月,鄭經長子鄭克臧被暗殺,馮錫範等人擁立年僅十二歲的鄭克塽繼承王位,借以把持“朝政”。
康熙皇帝在實行“沿海遷界”的同時,還大膽啟用降將施瑯,募練水師。康熙二十二年(1683年)八月,施瑯率清軍水師攻陷澎湖,鄭克塽在劉國軒的勸說下奉臺灣本島投降。
康熙三十九年(1700年),康熙帝下達詔令:“朱成功系明室遺臣,非朕之亂臣賊子”。隨後,清廷將鄭成功、鄭經父子靈柩遷往福建南安重新安葬,並“建祠祀之”。
漂泊於滄海的落葉,終於歸根了!
朱由榔出了國,清軍攻勢暫停,李定國率永歷軍隊殘部在滇西煎熬,雲南的局勢突然平靜了下來。我們再換壹次臺,將目光轉向東南,看看號稱“遙奉永歷政權”的鄭成功這些年到底在幹什麽。
李定國兩次進軍廣東,鄭成功連“打醬油”的興趣都沒有,直接導致“三南並舉”的中興局面化為泡影。前面說過,鄭成功不出兵,主要是擔心破壞與清廷和議的局面,這事還要從清廷策略的轉變說起。
隨著抗清進入“高潮期”,需要清軍頻繁調兵、用兵的包括三大戰區:西南戰區(孫可望)、兩廣戰區(李定國)和東南戰區(鄭成功、張名振)。以清軍的實力,應付三線作戰的局面確實有極大的難度。由於戰場分散,清軍雖然頻繁用兵,但往往收效甚微,除了舟山收拾得比較幹凈以外,四川、湖南、廣東、福建都陷入僵持的局面。
負責作戰的兵部雖然疲於奔命,但總的來說還能支撐。軍隊多跑路算是拉練,多打仗算是演習,養這麽壹群人不就是幹這個的嗎!
負責財政的戶部就比較慘了,朝廷運轉需要錢、兵部打仗需要錢、刑部辦案需要錢、禮部擺譜需要錢、工部建設需要錢、吏部發工資也需要錢,戶部又不是孫悟空,缺什麽變什麽。眼看國庫日漸空虛,戶部的黑鍋越背越大。
清廷上下,從順治帝到各部官員,都有壹個普遍的共識:繼續這樣打下去,肯定是不行的!
話雖如此說,但三大戰區的抗清武裝又不聽清廷的指揮,妳讓他消停他就能消停,怎樣才能扭轉局面?
永歷六年(1652年)初,壹封密奏送到了順治帝的案前,讓順治帝眼前壹亮,不禁豁然開朗。密奏只講了壹件事:利用鄭芝龍,招撫鄭成功!
高,實在是高!只要能摁住鄭成功,清軍就能放開手腳大幹壹場,先在兩廣收拾李定國,再揮師殺到西南清剿孫可望,最終平定天下!
說幹就幹,清廷馬不停蹄地做著準備工作,主要有三件事要做:
第壹,冊封鄭芝龍為同安侯,授予其子鄭世忠為二等侍衛,並提高生活待遇,大加籠絡。
第二,敕諭浙閩總督劉清泰,適度調整政策,為招撫營造友好氛圍。
第三,追查鄭成功家產遭搶奪壹案,將當年率軍進攻廈門的張學聖、馬得功、黃澍、王應元等人革職查辦。
“過場”演完,正戲正式開場。永歷七年(1653年)四月,浙閩總督劉清泰奉朝廷之命,開始與鄭成功接洽招撫事宜。
此次招撫,無論從動機來看,還是就行動而言,清廷無疑是相當有誠意的。招撫能否達到預期目的,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鄭成功的態度。
雖然鄭成功對永歷政權壹向愛理不理、若即若離,但對待清廷的態度卻是相當堅決的。
隆武帝“當盡忠吾家,無相忘”的囑托,鄭成功不會忘記!
曾經苦勸父親“虎不可離山,魚不可脫於淵;離山則失其威,脫淵則登時困殺”,鄭成功不會忘記!
母親田川氏受清軍淩辱而選擇自盡,鄭成功更不會忘記!
讓老子投降?妳沒睡醒吧?
鄭成功是政治家,不是“楞頭青”。——“楞頭青”只會感情用事,政治家善於深藏不露。
面對清廷拋過來的橄欖枝,長年因糧餉發愁的鄭成功決定陪他們玩玩兒,上演壹出“和平換食品”的好戲。(將計就計,權借糧餉,以裕兵食也。)
清廷提出“和議”,鄭成功沒有表示反對,而是搶先提了壹個意見:金礪大軍就擺在我家門口,妳們準備用嘴巴談判還是用火炮談判?
清廷從鄭成功的話中感覺到有譜,趕緊在六月調金礪部離開福建,壹方面表達“和議”的誠意,壹方面也是出於對付孫可望、李定國的需要。
搬開堵在家門口的“太師椅”,鄭成功趁機派軍前往福建、廣東沿海征兵買糧,賺得盆滿缽滿。
永歷八年(1654年)二月,清廷冊封鄭成功為海澄公的敕印抵達福州。這讓鄭成功有點措手不及:閑著沒事跟妳們玩玩兒,怎麽還當真了?
為了防止假戲真做,鄭成功立即表明態度:受封可以,剃發免談!他明白,只要不變發型,這敕印就發不下來。
清廷來使也怒了:妳怎麽提上褲子就不認人呢?
鄭成功不管這麽多,索性打著“海澄公”的旗號,派部隊到清軍控制的地區大肆征糧。那群地方官搞不清楚狀況,打又不敢打,只能乖乖交糧,回頭再向朝廷伸手要。(有司莫知攸措,剿撫兩無適從。)
壹方認認真真,壹方逢場作戲,時間壹長難免穿幫。北京的壹些大臣發現不對勁,還沒談出啥結果,糧食損失不計其數,搞得福建、廣東沿海各地苦不堪言。順治帝也察覺到鄭成功是個“大忽悠”,準備結束“和議”,繼續付諸武力。
清廷的態度陡然生變,鄭芝龍急眼了:鄭成功妳個小兔崽子,這不是把妳親爹往黃泉路上送嗎?!
為了保命,鄭芝龍屢次上疏,要求再做壹次招撫的努力,並提議讓兒子鄭世忠前往福建勸降。鄭芝龍如此誠懇,前期“和議”也確實忽略了打親情這張牌,順治帝決定再試壹次。能和平解決,誰願意幹仗啊,就像蔣介石所說“和平未到完全絕望之時,決不放棄和平”。
永歷八年(1654年)八月,鄭世忠跟隨清廷“和議”官員抵達福州,開始勸降。鄭成功還是老套路:只要不剃發,什麽都好談!踩過清廷紅線的態度沒有變化,地盤方面的要價卻越來越高,鄭成功壓根就沒想談成,“和議”再次陷入僵局。
鄭世忠著了慌,苦口婆心地勸鄭成功“不看賊面看父面”,總不能置親生父親於死地吧?
忽悠了這麽久,鄭成功總算在自家兄弟面前說了壹句肺腑之言:“吾不剃發即可保全父命,剃發則父命休矣。”——沒了利用價值,豈止是鄭芝龍性命堪憂,鄭家老小都會全部玩完!
十壹月,清漳州千總劉國軒、守備魏標因對上司不滿,主動派人找鄭成功接洽投降。眼看清廷逐漸清醒,繼續“忽悠”已經沒有市場,鄭成功決心利用這次機會大擴地盤。
十二月初壹,鄭成功派洪旭、甘輝部奪取漳州,又相繼攻克同安、南安、惠安、安溪、永春、德化、仙遊等地,對泉州形成鐵桶合圍之勢。
壹方如夢初醒,壹方原形畢露,“和議”已絕無可能,順治帝終於下定最後決心,付諸武力。
十二月,清廷任命濟度(濟爾哈朗世子)為定遠大將軍,率滿、漢軍進剿福建。次年二月,失去利用價值的鄭芝龍被囚禁,幾年後被清廷處死。
得知濟度大軍南下,鄭成功深感鄭軍陸戰能力薄弱,決定揚長避短,主動放棄先前占領的漳州、泉州兩府屬縣,並進行堅壁清野,集中兵力固守廈門、金門。同時,鄭成功又派出兩支水師分別前往浙江、廣東襲擾,牽制濟度大軍對福建的清剿。
由於鄭軍在廈門、金門防守嚴密,又有水師助防,再加上浙江、廣東相繼告急,濟度大軍在福建並無太大作為。清廷此次用兵的主戰場,反而轉移到了浙江、廣東沿海。
浙江方面,鄭軍的攻勢相當迅猛。
永歷九年(1655年)十月,鄭成功派出的甘輝、王自奇部會同從崇明島南下的張名振部發起舟山戰役,守島清軍來不及反應便遭全殲,鄭軍壹舉收復舟山。
十壹月,鄭成功為了加強廈門、金門防禦,命甘輝返回福建,調陳六禦前往舟山統管各部。
此後不久,張名振突然神秘死亡。關於死因,各種史料意見不壹,主要有三種說法:
第壹種說法是病死。這個說法比較合理,也最簡單,但時間未免有些巧合。更令人生疑的是,張名振臨終前將“浙系”舊部托付給了張煌言,鄭成功卻下令陳六禦將“浙系”全部收編。
鄭成功如此趁火打劫,便產生了第二種說法:張名振是被鄭成功暗害的!這個說法有壹定的合理性,但缺乏足夠的證據。另外,如果暗殺張名振,要承擔真相泄露、“浙系”嘩變的風險。以鄭成功謹小慎微的性格,不大可能冒這種風險。
第三種說法出自清江南總督馬鳴珮的壹封揭貼。揭貼上說,根據壹個投降的南明軍士兵交待,鄭成功要追究張名振進攻崇明失利的責任,準備抓他回廈門處死,張名振就被嚇死了。
盡管情節有些離譜,普通士兵掌握的信息很可能來自舟山的“路邊社”,但我覺得這種說法的可信度最高。
首先,張名振是“溶浙、限浙”的最後壹塊絆腳石,鄭成功有幹掉他的動機。其次,張名振手下都是鐵桿“浙系”,鄭成功必須考慮“維穩”問題,不會輕易冒險。
因此,鄭成功要除掉張名振,必須找壹個合適的借口。前面說過,張名振三入長江卻無果而終,崇明又沒能打下來,“浙系”內部的壹些將領已經開始對他頗有微辭。鄭成功以這個由頭找張名振的麻煩,阻力明顯要小得多,也不會授人以柄。當然,鄭成功大可不必置張名振於死地,士兵的道聽途說是不可靠的。
此時,張名振確實是病了,長年征戰讓他的身體嚴重透支。更主要的還是心病,是“信而見疑,忠而被謗”的痛苦。經鄭成功這麽壹攪和,張名振郁郁而終,撒手人寰。
再來看廣東方面,鄭軍的局面卻不容樂觀。
八月,鄭成功派黃廷、萬禮部赴潮州征糧,圍攻揭陽長達壹個多月之後攻陷,九月又相繼拿下普寧、澄海,開局還算不錯。
不過,李定國此時已經撤回廣西,尚可喜、耿繼茂、李率泰(時任兩廣總督)迅速抽調許而顯、徐成功部,會同潮州總兵劉伯祿、饒平總兵吳六奇增援潮州。十二月二十四日,各部援軍抵達潮州城下,與城內鄭軍展開對峙。
雙方對峙了兩個月,黃廷采納部將蘇茂的建議,率部出城與清軍決戰。鄭軍在釣鰲橋遭到清軍伏擊,損失四千多人,接著又在東村渡遭遇慘敗,實際上已無力固守,被迫撤回廈門。
抵達廈門後,怒火中燒的鄭成功將蘇茂處斬,黃梧、杜輝等部將也遭到責罰。
永歷十年(1656年)六月,被派往海澄鎮守的黃梧、蘇明(蘇茂的胞弟)發動叛亂,向清軍投降。鄭成功痛失重要的物資貯存地海澄,於七月“以牙還牙”,占領福州附近的閩安鎮,並以此為前沿,不斷對福州實施襲擾。
壹直到次年九月,浙閩總督李率泰趁鄭成功進攻臺州之機,率大軍奪回閩安鎮,鏟掉了這個距離福州不遠的“釘子戶”。
八月,清軍也在浙江采取動作,派宜爾德、田雄進攻舟山,鄭軍遭遇慘敗,陳六禦陣亡,張煌言率“浙系”殘部輾轉於浙江沿海繼續鬥爭。
為了鏟除後患,清軍將舟山島居民趕回大陸,房屋全部焚毀,“浙系”昔日的抗清中心變成了壹片廢墟。
自舟山戰役後,由於清廷正集中精力組織西南戰役,東南的局面逐漸轉入相持階段。
直取南京
清廷忙著收拾西南殘局,鄭成功卻沒打算消停消停。對峙壹段時間後,鄭成功開始蠢蠢欲動,著手準備壹次聲勢浩大的軍事行動——長江戰役!
鄭成功為什麽選擇打江南?為什麽選擇在這個時候打江南?
按照鄭成功自己的說法,他決心進取南京,光復前明。(提師望復神京,以復社稷。)另外還有壹種看法,認為鄭成功是想通過在長江下遊點火,牽制清軍對永歷政權的剿殺。
從鄭成功的個人性格和處事方式來看,這兩種說法的可信度基本上為零。
自從高舉抗清旗幟以來,鄭成功向來只顧及“閩系”的自身利益,帶著“閩系”幾十萬大軍在東南沿海自行其是。無論是對鄰近的“浙系”,還是自己聲稱“遙奉”的永歷政權,鄭成功均采取置若罔聞的態度,任其自生自滅。
鄭成功的這種想法,在李定國出征廣東時表現得尤為明顯。李定國兩次聯絡他合擊廣東,鄭成功表面上拍胸脯,實際上毫無實質行動,甚至都懶得“圍觀”。
除了擔心“忽悠”清廷的策略受到影響以外,鄭成功最擔憂的是萬壹與永歷政權連為壹體,“閩系”將受到朝廷的制約,使自己的利益受損。
就這麽壹號人,說他是以復國為己任、替永歷分憂,妳當天下人都是三歲小孩兒?
鄭成功向來以“閩系”的利益為核心,因此分析他打江南的動機,還得立足於“閩系”面臨的處境。
由於“和議”破裂,清廷對福建、浙江、廣東強化了軍事存在,鄭成功雖然坐擁幾十萬大軍,但地盤實在小得可憐,除了廈門、金門稍微成片壹點,剩下的基本上都是遍布東南沿海的小島。所謂的“閩系”,其實就是“端著銀碗沒飯吃”的“海上漂”。
自從壟斷海外貿易之後,“閩系”的銀子顯然不是問題,硬要說有問題,無非是沒地方放、沒地方花。
地盤問題與糧食問題相輔相成,壹直是困擾“閩系”發展的兩大瓶頸。鄭成功原本借助清軍漳州兵變奪取了很大壹塊地盤,但由於動作太大,觸動了清廷的神經。“主戰派”徹底壓垮“主和派”,清軍大兵壓境,鄭成功被迫選擇放棄。即使趁著清軍回撤重新占領,這些地區也早被鄭軍撤退時的堅壁清野搞得餓殍遍地,根本無法立足。
在這種情況下,鄭成功要想維系“閩系”大軍的生存,就必須開辟“新天地”。反復權衡之後,鄭成功將目標鎖定在了以南京為中心的江南地區,理由主要有六條。
其壹,大量前明義士和“潛伏”的抗清武裝集中在江南,鄭軍能有充足的後援。
其二,鄭成功在永歷十二年(1658年)正月被永歷朝廷冊封為延平王,感召力顯著增強。
其三,江南地區經濟發達,糧食充裕、地盤廣大。
其四,奪取南京具有“毀三觀”的重大政治意義,能夠極大地提升鄭成功的政治地位和影響力。
其五,江南地區的抗清鬥爭已沈寂多年,清廷又集中精力收拾西南、華南殘局,在長江下遊地區兵力空虛。
其六,清軍擅長陸戰,水師則剛剛起步,鄭軍由海入江,可充分發揮水師的優勢,揚長避短,取勝更有把握。
打定主意之後,鄭成功趁清軍調集大軍進攻西南之機,與張煌言的“浙系”壹起,著手準備揮師長江,奪取新的抗清根據地。
永歷十二年(1658年)五月,鄭成功率部抵達浙、閩邊界的沙埕壹帶,會同張煌言部於六月進攻瑞安。鄭成功派兵到溫州等地籌集糧餉後,於六月至七月間揮師北上,抵達舟山島,搭建草蓬駐紮。這座清軍留下的廢墟,再壹次成為抗清的前沿陣地。
八月,鄭成功率水師進抵羊山(今大洋山),於初十召集“閩系”、“浙系”主要將領召開軍事會議,商討進軍長江的具體部署。
就在萬事即將俱備之時,“東風”卻提前來了,而且相當給力,壹場颶風光臨羊山。敵人進攻可以還擊,颶風來襲就只有幹瞪眼了。鄭軍損失相當慘重,鄭成功打仗又喜歡帶著家屬,結果六位妃嬪、三個兒子都被刮到海裏淹死了。
鄭成功大為震驚,只得宣布散會(其實早被吹散了),率部返回舟山。舟山已成壹片荒島,沒辦法長期立足,鄭軍又於九月南下福建。
還沒動手就挨了當頭壹棒,鄭成功抑郁得想撞墻,壹路上直拿沿海的清軍出氣,相繼攻克臺州、海門衛、黃巖、樂清等地,最後返回金門休整。
永歷十三年(1659年)二月,鄭成功、張煌言再次準備北上長江。四月底,鄭軍進抵浙江定海,經兩日激戰後全殲守軍。
鄭成功攻占定海,本意是想造成進攻寧波的假象,調出駐防江南地區的清軍前往浙東增援。清軍果然中計,兩江總督郎廷佐調兵馳援浙東,江南地區的防守更加薄弱。
五月初,鄭成功、張煌言率十萬大軍、三千多艘戰船從定海北上,於十九日經吳淞口進入長江。
在強大的鄭軍水師面前,清軍在長江的防禦體系純屬小孩兒“過家家”。鄭成功經過江陰時,嫌地方太小,打都懶得打,大搖大擺就過去了。壹直到六月十六日,大軍才像模像樣地在瓜州打了第壹仗。二十二日,鄭軍在鎮江大敗蔣國柱、管效忠的援軍,兩日後占領鎮江。二十六日,張煌言率領的前鋒部隊已進抵南京城下。
得知南京告急,清廷舉朝震驚,輿論壹片嘩然。
德國傳教士湯若望當時在北京為清廷效力,根據他的描述,遭遇這場突然的變故,順治帝瞬間秀逗了,打算卷起鋪蓋回東北老家。挨了孝莊太後壹頓臭罵之後,順治帝才漸漸平心靜氣,與廷臣商討應對之策。
朝堂如此,坊間的混亂更是可想而知。當時的北京人心惶惶,很多人甚至產生了南下投奔鄭成功的想法。(東南之客,皆惶怖思歸,至有泣下者。)
由於清軍主力集中在西南進剿朱由榔、李定國,北京已經無兵可派,只有在六月底急調進攻貴州的部分八旗兵回援南京。
這支援軍有兩個特點:數量極少、身心疲憊。——兵力有限也就算了,居然還是在貴州被揍得鼻青臉腫,被其他輪戰部隊換下來休整的,這玩笑開大了吧?
無論這支援軍是否能趕到南京,就目前雙方的態勢來看,鄭成功、張煌言拿下南京城已然是十拿九穩。但是,不怕壹萬就怕萬壹,走過南明十幾年的歷程,我們應當對壹切莫名其妙的意外有足夠的心理準備。
不錯,意外再次光臨。——鄭成功占領鎮江後,竟然不走了!
鄭成功進長江之後,迅速地往南京趕,還派張煌言率“浙系”打頭陣,卻決定在鎮江原地踏步,著實令人有些費解。
鄭成功到底在搞什麽飛機?
其實,鄭成功最初的想法是在鎮江作短暫停留,通過搞入城式、閱兵式,向江南各地“亮肌肉”,以達到“不戰而屈人之兵”的戰略目的。
鄭成功采取的策略,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。南京附近的句容、儀真、滁州、六合紛紛派人前來聯絡,表示願意歸附。
二十八日,鄭成功在鎮江舉行軍事會議,討論進取南京的具體作戰部署。
要進攻堪稱“江南首府”的南京,這麽大的作戰行動確實有必要討論壹下。但是,事情壞就壞在這次會議上,確切地說,壞在會議的決策上。
這次軍事會議主要討論壹個問題:怎麽去南京?
甘輝首先發言,建議大軍棄船登岸,走陸路長驅直入,打清軍壹個措手不及。(狡虜亡魂喪膽,無暇預備,由陸長驅,晝夜倍道,兼程而進,逼取南都。)大軍能壹鼓作氣拿下最好,實在攻不下來,就先困住南京守軍,掃清外圍,“孤城不攻自下”。
這裏涉及壹個水路、陸路孰快孰慢的問題,前面曾經說過壹個類似的場面。劉文秀進攻常德時,自己率主力走陸路,部將盧明臣則走水路,意圖兩路合擊。結果,“衰神”劉文秀被暴雨攔在半道,盧明臣卻順江跑得飛快,導致兩軍難以相顧,盧明臣的孤軍幾乎全軍覆沒。
看來,水路顯然比陸路要穩妥得多。但是,打仗是門藝術活,更是門技術活,具體情況還得具體分析。從鎮江到南京,不僅是逆流而上,在這個季節還是頂風而行,這對主要依靠風力前進的戰船而言,顯然是很不利的。特別是鄭軍水師都是在海裏晃蕩的,戰船的噸位壹個比壹個大,如果風不給力、水不給力,大噸位就成了大麻煩。
因此,走陸路輕裝突襲南京,顯然要靠譜得多。
但是,大部分將領堅持認為,鄭軍擅長水戰、不習陸戰,又值酷暑雨季、河流猛漲,陸路進軍有諸多不便。(我師遠來,不習水土,兵多負重,值此炎暑酷熱,難責兼程之行也。)
兩種意見已經擺到了桌面上,接下來就該輪到鄭成功拍板了。
現實的情況往往很復雜,不可能有完美無缺、無懈可擊的解決方案。所謂決策,不過是“兩害相權取其輕,兩利相權取其重”。
鄭成功最後做出的決定是走水路!
事實證明,鄭成功失策了。
鄭成功帶著黑壓壓的“大家夥”從鎮江逆長江而上,江面越走越窄,就跟大胖子擠小巷子似的,根本活動不開。再加上頂風逆水而行,戰船只能靠兩岸的纖夫拉動,速度可想而知。
“爬”了十天,鄭成功的大軍終於在七月初九進抵南京郊外。
慢是慢了點,但清軍的大批援軍尚未抵達,攻破南京應該還有壹點時間。遺憾的是,鄭成功又“抽風”了,接下來幾天的行程是這樣安排的:
七月初九,到達,休息。
七月初十,休息。
七月十壹日,到鐘山觀光,熟悉地形。(繞觀鐘山,采踏地勢。)
七月十二日,祭奠太祖。
七月十三日,部署圍困南京。
毫不誇張地說,從鎮江召開的軍事會議開始,鄭成功就沒走正確過壹步棋。
該走陸路的時候,他走水路,結果磨蹭了十來天。
該順勢開火的時候,他要休息觀光,真搞不清楚坐船過來的能有多疲憊。(暈船?搞錯沒有,人家都是大海裏混的,走長江會暈船,誰信啊?)
兩次磨蹭也就算了,該壹鼓作氣發起進攻的時候,鄭成功竟然選擇圍而不攻,想讓南京不戰而降,妳以為南京是福建的小縣城?
正是因為南京太大,鄭軍根本圍不過來。七月中旬,清軍援軍陸續抵達,包括蘇松水師總兵梁化鳳、浙閩總督趙國祚、浙江巡撫佟國器,還有南京上下遊的清軍紛紛向南京靠攏。鄭軍圍得不嚴實,這些援軍全部乘隙進入南京城,力量對比正在悄然生變。
鄭成功圍而不攻,想“不戰而屈人之兵”。鄭軍士兵剛開始興致挺高的,但過了沒幾天,看領導沒啥動靜,也就放松心情了。閑著也是閑著,大家盔甲、武器甩壹邊,全跑長江裏捕魚去了。
七月二十二日,梁化鳳、管效忠分別率兵從儀鳳門、鐘阜門出城,向鄭軍發起反攻。負責圍困此處的是余新等部,鄭軍士兵有的在捕魚,有的在烤魚,還有的在睡大覺,結果被打得鬼哭狼嚎,主將余新也被清軍活捉。
次日,南京城內的清軍發起總攻,鄭軍的包圍圈徹底瓦解。混戰之中,甘輝、萬禮被俘,鄭成功只得率殘部順江撤退。
八月十壹日,鄭成功進攻崇明縣城未果,率部逃往福建。
勝券在握的長江戰役被鄭成功打成這副鳥樣,率“浙系”配合作戰的張煌言確實沒有意料到。讓張煌言更郁悶的是,鄭成功實在太不地道,竟然把“浙系”甩在南京上遊,自己帶著“閩系”先跑了,還有沒有壹點職業道德?
張煌言跟鄭成功在七月初五見過壹面,當時鄭成功拍著胸脯保證說,“閩系”打南京綽綽有余,“浙系”沒必要在南京浪費時間,應當迅速向上遊推進。張煌言也覺得有理,趕緊率“浙系”逆江而上,於七月初七抵達蕪湖。
“浙系”的兵馬不多,陣勢沒有“閩系”龐大,靠這點人根本沒辦法攻城略地。不過,張煌言有辦法,他打出“延平王”的旗號,發布招撫檄文。
張煌言這招果然奏效,不出壹個月,共有四府(太平、寧國、池州、徽州)、三州(廣德、無為、和陽)、二十四縣(當塗、寧國、宣城等)宣布歸附。各地派來的使者跟朝拜似的,紛紛雲集蕪湖。
張煌言還在寧國府接受新安(今安徽歙縣,與徽州府縣同城)的歸降,南京戰敗的消息便傳了過來。張煌言驚出壹身冷汗,大喊壹聲:“不好!鄭成功肯定要跑!必須把他攔住,不然我們就成替死鬼了!”
事不宜遲,必須迅速派人前去阻攔鄭成功。可是,“浙系”的人有壹個算壹個,都被派往各地招撫去了。張煌言實在派不出人,只得找壹位和尚,帶著自己的書信去追鄭成功。在書信中,張煌言苦口婆心地勸鄭成功留在江南,跟自己壹起堅持抗清鬥爭。(上遊諸郡邑俱為我守,若能益百艘來助,天下事尚可圖也。)
但是,鄭成功跑得飛快,和尚哪裏追得上。即便追上了,以鄭成功的為人,應該也不會鳥他。
張煌言成了“棄兒”,只有自己想辦法生存。此時,兩江總督郎廷佐已經騰出手來,準備圍剿張煌言,從荊州趕來支援南京的清軍也已經抵達安慶。腹背受敵的張煌言決定逆江而上,迎戰缺乏水戰經驗的荊州清軍,進入鄱陽湖區之後再另想辦法。
八月初七,張煌言與荊州清軍在蕪湖附近相遇,雙方激戰後互有傷亡。由於遭到鄭成功的拋棄,“浙系”早已軍心浮動。當晚,不知南京已經解圍的荊州清軍不想再繼續糾纏,發炮準備啟航。聽到炮聲,已成驚弓之鳥的“浙系”軍隊誤以為清軍來攻,紛紛逃散、潰不成軍,張煌言被迫改乘小船進入巢湖。
張煌言采納了當地抗清義士的建議,棄船登岸,準備前往皖鄂交界的英山、霍山地區。八月十七日,張煌言壹行抵達霍山邊緣,遭到已歸附清軍的褚良甫部阻截。走投無路的張煌言“變服夜行”,經安慶、建德、義烏、寧海等地奔向大海,歷時半年之久,終於與留在浙江沿海的“浙系”殘部會合。
向臺灣進發
長江戰役以失敗告終,鄭成功再次回到了原點,繼續考慮壹個越來越嚴重的問題:往哪裏去?
再入長江?——不靠譜,清軍已經被“打草驚蛇”,就算能進去,恐怕也出不來。
立足福建擴地盤?——更不靠譜,鄭軍雖然有點騎兵,但根本不是八旗兵的對手。即使趁人不備勉強占幾個縣城,清廷援軍壹到,還得堅壁清野往後撤,太麻煩。
天下之大,卻無處安身,鄭成功的心拔涼拔涼的,打算熬得壹天算壹天。
就在鄭成功瀕臨絕望的時候,壹個人的到來,點燃了他心中即將熄滅的希望之火。鄭成功聽完這個人的話,情不自禁地拍案而起,先前還黯淡無光的雙眼瞬間炯炯有神。
在長江、福建都不靠譜的情況下,已經初顯暮氣沈沈的鄭成功終於看到了希望的曙光——臺灣!
前來投奔鄭成功的人叫何斌,原本是荷蘭東印度公司招募的“當地職員”,而且職位還不低。
何斌是從臺灣逃回大陸的,荷蘭人盤踞臺灣也不是壹年兩年了。早在萬歷三十二年(1604年),荷蘭人就曾染指澎湖,後來被明朝軍隊揍跑了。天啟二年(1622年),荷蘭人卷土重來,不僅重新占據澎湖,還向臺灣本島滲透。兩年後,明朝軍隊收復澎湖,卻對尚未設立行政機構的臺灣本島不屑壹顧。從此,荷蘭人得以在臺灣立足,並以東印度公司的名義開始了殖民統治。
何斌詳細介紹了臺灣的地形地貌,其實鄭成功早就掌握這些情況。他雖然沒去過臺灣,但鄭氏集團長年壟斷海外貿易,從鄭芝龍開始就跟臺灣有貿易來往,鄭軍內部熟悉臺灣的人不少。
鄭成功不是沒有想過去臺灣發展,但搞不清楚對方實力如何、自己能不能拿下,因此始終下不了最後的決心,畢竟鄭軍再也經不起任何折騰了。
作為荷蘭東印度公司旗下的高級官員,何斌對荷蘭人在臺灣的布防情況了如指掌。在向鄭成功和盤托出後,何斌又給出了壹個相當權威的結論:國姓爺收拾那幫紅毛,小菜壹碟!
打定主意之後,鄭成功開始著手準備,壹找向導二籌糧。找向導不難,鄭軍內部就有不少。只有糧食比較麻煩,還是得靠打秋風,要麽找浙江,要麽找廣東,需要壹點時間準備。
永歷十四年(1660年)初,鄭成功的籌糧隊伍還沒出發,奉命清剿鄭成功的達素大軍就南下福建,復臺計劃被迫暫時擱置。
由於廈門、金門城防堅固,清軍又不習水戰,達素沒有取得預定戰果,勉強對陣幾個月後北撤。年末,鄭成功的籌糧大軍終於開拔,前往潮州。
永歷十五年(1661年)正月,鄭成功召集高級將領在廈門召開了壹次秘密軍事會議,議題只有壹個——復臺。
在這次會議上,鄭成功第壹次小範圍公開了復臺的戰略計劃。出乎他意料的是,這個計劃剛拋出來,便遭到壹片激烈反對。
部將吳豪率先“吐槽”,提出了三大反對的理由:
其壹,從大陸攻打臺灣“水路險惡”。
其二,荷蘭人“炮臺利害”。
其三,臺灣“風水不可,水土多病”。
總而言之,言而總之,去臺灣不容易,打臺灣更難。即使撞大運打下來,想在那個鬼地方活下去更是難上加難!
吳豪去過臺灣,發言比較有權威性。大多數將領本來就不願意遠離故土,聽了吳豪的話,也紛紛搖起腦袋,認為此事不妥。
眼看復臺的計劃就要黃了,部將馬信突然站出來,堅定支持鄭成功的復臺計劃。
馬信先是替鄭成功講明了復臺的重大戰略意義:打臺灣,是要尋求更廣闊的根據地,以利於長期堅持抗清鬥爭。(藩主所慮者,諸島難以久拒清朝,欲先固其根本,而後壯其枝葉,此乃終始萬全之計。)
接下來,馬信從戰術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想法。
首先,打仗肯定是有困難的,但任何地形、任何敵人都是有相應的辦法去對付的。(紅毛雖桀黠,布置周密,豈無別計可破。)
其次,咱們閑著也是閑著,偵查壹下未為不可,能打就果斷打過去,萬壹不能打,再作商議也不遲。(今乘將士閑暇,不如統壹旅前往探路,倘可進取,則並力而攻;如果利害,再作商量,亦未為晚。)
馬信有理有據、言辭懇切,壹邊倒的態勢得以緩解,特別是鄭軍元老楊朝棟也表示贊同,使會議的氣氛發生了扭轉,多數將領紛紛鼎立支持。
最終,廈門會議達成了來之不易的共識。鄭成功的喜悅溢於言表,當即拍板定調,準備武裝復臺。
馬信替鄭成功講得很清楚,復臺是擴地盤,而不是“搬家”,拿下臺灣的同時,大陸沿海的前沿陣地也是不能丟的。
因此,鄭成功對沿海基地的布防做了周密的部署:
——世子鄭經率洪旭、黃廷、王秀奇等部鎮守廈門,並由鄭經全權調度沿海各島。
——鄭泰、蔡協吉兩部鎮守金門,同時支援廈門大本營。
——洪天祐、楊富、楊來嘉、何義、陳輝等部分別駐守南日、圍頭、湄州各島,策應金門守軍。
——陳霸部鎮守南澳,牽制廣東清軍趁虛而入。
——郭義、蔡祿兩部調防銅山,加強張進部的防守力量,策應南澳守軍。
永歷十五年(1661年)正月,鄭成功舉行誓師大會,正式向全軍公開了復臺計劃,收復臺灣進入最後的倒計時。
輾轉抵達浙江沿海的張煌言得到消息,趕緊給鄭成功寫了壹封信,表達了自己的意見:這不科學!
客觀地說,從東南沿海的態勢來看,復臺是唯壹正確的選擇。張煌言身在浙江,不太了解鄭成功面臨的具體困難,反對是情有可原的。
最重要的是,鄭成功在長江戰役中扔下“浙系”自己跑掉,讓張煌言難免心存芥蒂。因此,他對鄭軍復臺的真實目的產生了質疑,認為鄭成功這樣做,是想遠離戰禍、偏安壹隅。(不過欲安插文武將吏家室,使無內顧之憂。)
壹竿子捅這麽遠,誰知道妳是去幹什麽?
張煌言有意見,但反對無效,鄭成功根本沒工夫搭理他。——自己玩自己的去,管閑事還輪不到妳!
二月初三,鄭成功率大軍出海,次日抵達澎湖,留下陳廣、楊祖等部鎮守。初八,鄭軍前鋒在臺灣本島的鹿耳門(今臺南安平鎮附近)強行登陸,並在幾千中國人的協助下建立灘頭陣地,大批戰船隨即駛抵赤嵌城(今臺灣臺南)海灣。
荷蘭在臺灣有軍隊壹千多人,由長官揆壹統壹指揮,主要駐防在熱蘭遮(今臺南安平古堡)和赤嵌城附近。鄭軍水師主力首先向赤嵌城海灣的荷軍水師發起強攻,荷軍戰船雖然只有三艘,但噸位大、火力強、射速快,剛壹交火就給鄭軍水師造成很大的傷亡。不過,鄭軍水師有六十多艘戰船,在數量上占據壓倒性的優勢,靠擠也能將對方擠兌死,荷軍占不了什麽便宜。
壹場激烈的炮戰之後,荷軍戰船有壹艘被擊沈,另外兩艘負重傷後倉皇逃竄,海戰勝利結束。
海面酣戰的同時,先期登陸的鄭軍也向荷軍陣地發起猛烈攻擊,以排山倒海之勢沖向敵陣。荷軍雖然單兵裝備優良,但難敵“人海戰術”,紛紛退入城內固守。二月初十,鄭軍攻占赤嵌城,揆壹率殘部龜縮在熱蘭遮負隅頑抗。
三月二十九日,鄭成功向荷蘭軍隊下達最後通牒,揆壹咬牙死扛,繼續固守在熱蘭遮城內,等待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援軍。
五月,鄭軍第二梯隊抵達臺灣,熱蘭遮已經唾手可得。
就在鄭成功準備最後壹戰時,駐防銅山的蔡祿、郭義於六月初三發動叛亂。鄭經雖然早就懷疑這兩人有反意,但壹直沒有采取反制措施。
得知銅山叛亂後,鄭經才匆忙從廈門調集軍隊進剿。十九日,叛軍將銅山搶劫壹空後,從容投奔清軍,廈門軍隊撲了空,看到的只是銅山的壹片焦土。
銅山叛亂雖然被“平息”,但嚴重幹擾了鄭成功的既定部署,轉而對熱蘭遮實施“鐵桶戰術”,令其不戰自降。
八月十二日,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援軍逼近臺灣,但看到前方鄭軍的戰船黑壓壓的壹大片,嚇得調轉航向跑掉了,揆壹最後的希望破滅。
十二月十六日,鄭成功趁部分荷蘭士兵出城投降之機,向熱蘭遮發起總攻。十八日,已陷入絕境的揆壹無條件投降,率殘部滾出臺灣。
此後,臺灣成為鄭成功抗清的大本營,與廈門、金門、南澳等地遙相呼應,攪得東南沿海的清軍不得安寧。
為了對付鄭成功,清廷從永歷十五年(1661年)八月開始,在浙江、福建、廣東等地實行“沿海遷界”。由於當時的臺灣尚未全面開發,鄭軍的糧餉主要依靠到大陸沿海“打秋風”補給,因此處境愈加困難。
永歷十六年(1662年)四月,朱由榔被俘的消息傳到東南,鄭成功的內心極其苦悶。永歷政權的傾頹,自私自利的“閩系”也做出了很大的“貢獻”。或許,鄭成功除了苦悶之外,難免有壹些愧疚與悔恨之情。
不過,當張煌言提出擁戴魯王繼統時,早已習慣於自行其是的鄭成功根本不屑壹顧,依舊以“延平王”的身份,打著永歷政權的旗號,繼續跟清廷死磕。
屋漏偏逢連夜雨,國事傾頹,家事也不安寧。留守廈門的鄭經與四弟奶媽通奸生子,謊報侍妾所生。鄭成功先是歡喜壹場,得知真相後急火攻心,加上早已積存於胸的悲憤,竟壹病不起。
彌留之際,鄭成功不禁悔恨交加、仰天長嘆:“我無面目見先帝於地下!”
五月初八,鄭成功在絕望與悲憤中溘然長逝,年僅三十八歲。
鄭成功去世後,張煌言又向鄭經提出擁戴魯王的動議。但是,鄭經比他爹還要差勁,除了嗤之以鼻外,還停發魯王的“宗祿”,任其自生自滅。十壹月十三日,四十五歲的魯王朱以海病逝。
鄭成功英年早逝,鄭氏集團在鄭經的領導下愈加混亂,文武官員陷入爭權奪利的內訌之中。康熙二十壹年(1682年)正月,鄭經病死,各派勢力加緊了篡權步伐。次月,鄭經長子鄭克臧被暗殺,馮錫範等人擁立年僅十二歲的鄭克塽繼承王位,借以把持“朝政”。
康熙皇帝在實行“沿海遷界”的同時,還大膽啟用降將施瑯,募練水師。康熙二十二年(1683年)八月,施瑯率清軍水師攻陷澎湖,鄭克塽在劉國軒的勸說下奉臺灣本島投降。
康熙三十九年(1700年),康熙帝下達詔令:“朱成功系明室遺臣,非朕之亂臣賊子”。隨後,清廷將鄭成功、鄭經父子靈柩遷往福建南安重新安葬,並“建祠祀之”。
漂泊於滄海的落葉,終於歸根了!